[摘要]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人相食”话语已逐渐生长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思想史上的一个观念和意义系统。以人类对“人相食”的怵惕哀矜的基本情感为起点,视其为常态化的规则、秩序与正义崩溃的表征,引发对执政者施政过程与绩效的批判检讨,强调政经文化精英乃至天下普通个体在世乱
引言:缘于“洞穴奇案”的思考
“洞穴奇案”(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是法学家富勒在1949年虚构的案例:五名洞穴探险者受困于洞穴中,水尽粮绝,为了活命,其中一人提议以抽签的方式选定一人供余众食用,但在抽签前此人反悔,而其他四人决意执行这一方案,最终此人被抽中并成为余众的食物,幸存四人获救后,被以杀人罪公诉。富勒据此演绎出五位大法官的判决,勾勒出不同法学流派的思维图景。1998年,法学家萨伯在富勒的案例与判决的基础上,新增了九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1]]至此,关于“洞穴奇案”形成了十四种基于不同法理的判决方案,也使这一虚构的案例成为当代西方法学知识中的经典和常识。
如果是中国法官审理“洞穴奇案”,判决将是怎样的 中国本土的法律思想资源将会孕育出何种面目的“洞穴奇案”判决 “人吃人”或“人相食”,这是以中国本土话语概括“洞穴奇案”案情的最简约答案。但是,在中国语境下,“人吃人”或“人相食”的表述均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被赋予政治修辞的属性。“人吃人”这一表述在五四后,经鲁迅《狂人日记》的阐发,承载了激烈的反传统意识,进而在左翼的历史叙事中成为“万恶的旧社会”的意象与象征;而“人相食”则是中国史中的一个固有的表述,承载着传统中国的一系列特定观念、价值与意义——在借助于“俗套”式的本土习语进行概括或“转述”之后,原本一个关于司法个案的中西法文化比较的问题,起首即已经溢出司法技术层面,而与宏大的历史和政治相勾连。就书写史而言,在文本中,“人相食”的表述通常是写实,与作为隐喻的“人吃人”的表述相比,有着更为久远的、长时段的存续期和影响力。本文以“人相食”这一中国史中的固有表述和现象为切入点,梳理和探寻在面临“人相食”困境乱象时,中国本土的法律思想资源提供了何种形态的认知与应对方案以及这些方案中蕴涵着哪些本源性的法理。
一、正史中的“人相食”话语和叙事
在正史中,“人相食”作为独立的、固定的短语,最早出现于断代史典范《汉书》中:“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2]]而且,这一短语在《汉书》的本纪、列传、志等不同门类中屡次出现。“所谓‘二十四史’的名称中,除了《史记》与《三国志》之外,有十三部称‘书’,九部称‘史’”;“每一部取法《史记》的史书,其名称都以‘史’字收尾,而以《汉书》为典范的史书则以‘书’字结尾。”此说可由宋朝前所有的正史轻易获得验证。只有二十四史的最后五部似乎与这个说法不相吻合。然而,更进一步的探究其原委,我们发现这个传统所以改变,具有意味深长的原因(一个传统并不会骤然消逝)。[[3]]对清代官方认定的正史——“二十四史”而言,《汉书》开创了主流的书写范式。“人相食”成为正史乃至其他类型的史籍中的固定表述,与《汉书》的影响力有关。
“人相食”这一表述在《汉书》中出现十余次,这个数量与频率在二十四史中名列前茅。《汉书》中的15项“人相食”记载,分别对应于西汉时期的9次出现了“人相食”现象的饥荒(或者说,西汉饥荒中的9次“人相食”被载入正史)。这9次大饥荒中,高祖时期1次(高祖二年)、武帝时期2次(建元三年、元鼎三年)、元帝时期3次(初元元年六月及九月、初元二年六月)、成帝时期1次(永始二年)、王莽时期2次。按照传统的历史观,高祖二年正处于“龙兴”之际,武帝时期则为国力强大的“盛世”,但这些时期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人相食”的景象。
《汉书》“人相食”的书写模式,有以下特征:
其一,从上下文的关联分析。“人相食”的上下文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类:施政举措(边事与内政)、议政策论(总结或褒贬)、天灾、异象、罪己诏。作为语辞,“人相食”具有历史叙事中的话语转换或推进的“中介”属性:或者作为不同施政举措的“中介”;或者作为不同策论间的“中介”;或者作为天灾、异象间的“中介”;或者作为天灾、异象与施政举措(惠政较为常见)之间的“中介”;或者作为天灾、异象、失误的施政举措与罪己诏之间的“中介”。
其二,从整体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分析。“人相食”三字在本纪出现4次,在列传出现3次,在食货志出现6次,在天文志与五行志各出现1次。15项“人相食”的记载,涉及高帝2次,其中1次在本纪、1次在食货志中;涉及武帝4次,其中1次在本纪、2次在食货志、1次在五行志;涉及元帝4次,其中2次在本纪、1次在列传、1次在天文志;涉及成帝1次,在食货志中;涉及王莽4次,其中2次在列传、2次在食货志。在列传中出现的“人相食”的功能:一次是为引出翼奉对元帝的直谏,两次是作为王莽篡政后的乱象,均与对人物的褒贬扬抑相关。在天文志与五行志中,“人相食”被视为“灾异”,则表明当时谶纬术数之学的发达和影响。在《汉书·食货志》中,“人相食”一语频频出现,俨然成为这一传统中国“民生法制大纲”的书写线索。
《汉书》开创了“人相食”一语在正史中的书写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常变交织。纵观《汉书》之后正史的“人相食”书写模式,有若干变化之处。
其一,因为战乱而导致的“人相食”显著增多。这往往发生在围城战的被围一方,“经年粮尽,遂杀人充食”。[[4]]这类记载在五代出现较频繁,如刘仁恭被围沧州,“城中食尽,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墐土而食,死者十六七”;其子刘守文、刘守光兄弟相杀,刘守文所部被围,城中食尽,“人相杀而食,或食墐土,马相食其騣尾,(吕)衮等率城中饥民食以曲,号‘宰务’,日杀以饷军。”;[[5]]杨行密被困扬州,“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6]]在围城战之外,粮绝薪尽的军队以民为食的各种情形也屡见不鲜。
其二,个案模式的“人相食”的记载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个案模式的“人相食”记载中,均未出现“人相食”三字,这反应了“人相食”的个案叙述在语辞层面“回避”了“人相食”这一固有表述。正史中,有关个案模式“人相食”的记载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壮志饥餐胡虏肉”型。[[7]]这是指饥荒时以敌方军民为食。如前秦苻登征伐姚苌,“是时岁旱众饥,道殣相望,登每战杀贼,名为熟食,谓军人曰:‘汝登朝战,暮便饱肉,何忧于饥!’士众从之,啖死人肉,輒饱健能斗。”[[8]]
第二种,“杀妾仆供军食”型。这类个案作为忠义事迹而被记载。如东汉末年“有雄气壮节”的臧洪,被袁绍围困,粮尽援绝,“杀其爱妾以食将士,将士咸流涕,无能仰视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叛离”;[[9]]唐代张巡与许远守睢阳,粮尽,“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 ’乃杀以大飨,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10]]
第三种,“食乱臣肉泄愤”型。如五代张彦泽为恶多端,滥杀官民,被耶律德光处死,“市人争破其脑,取其髓,脔其肉而食之”。[[11]]
第四种,“割股疗亲”型。这类事迹在孝义列传中较为多见。如明代儒生夏子孝,“九岁父得危疾,祷天地,刲股六寸许,调羹以进,父食之顿愈”。[[12]]对于“割股疗亲”的行为,法令的规制并不一致。洪武二十六年,一批“割股疗亲”的孝子被旌表,有的还被授以官职。洪武二十七年,山东日照民江伯儿刲肉疗母,不愈,祷于岱岳神,如母痊愈愿杀子以祀。后江伯儿果然如约杀死其三岁儿。太祖闻报大怒,认为“灭伦害理”,将其治罪,并命群臣讨论修改旌表例。讨论的结果是“自今父母有疾,疗治罔功,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13]]即对这类行为既不禁止也不鼓励。但是,永乐年间,一些割股疗亲的孝子又开始被朝廷纳入旌表之列。
第五种,“人肉之癖”型。如隋末朱粲以人肉为“味之珍宁”,“掠小儿蒸食之”[[14]];五代苌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为食”。[[15]]
这五种个案模式的共同点是,它们均不会在《食货志》中出现,与事关大范围地域内民众的公共民生的大饥荒无关。这些个案,有着“人相食”的实质内容,却并无“人相食”的冠名,这种表达方式加强了作为固有表述的“人相食”一语的意义和功能——这种语义现象与中国传统的“正名”论和“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相契。
总体而言,在帝制中国,“人相食”一语具有与众不同的修辞属性,承载着批判和质疑王朝的治理绩效与统治合法性的功能。在史籍的撰述过程中,“人相食”一语被史官以“显白”与“隐微”相结合的方式审慎运用,并被后世学者和史家在撰述时给予特别的对待。同时,某些类型的食人行为在正史中被允许、合法化,但在正史的叙事中并未被嵌以“人相食”这一固定表述,由此更能表明这一固定表述有着特定涵义。
二、地方志中的“人相食”话语和叙事
与正史相接续,“人相食”也是历代地方志描述灾荒的一个“固定搭配”。“一般地说,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16]]以光绪三年(1877年)、光绪四年(1878年)为例,华北出现了被史书称为“丁丑大祲”或“丁丑奇荒”的罕见旱灾,在这场旱灾中较为广泛地发生了“人相食”的景况。山西是这场灾荒的核心地带,损失惨重。以隰州为例,“光绪元年,户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大口六万七千零九十五,小口三万六千五百八十。光绪三年大祲,户一万零六十五内,大口二万一千一百三十三,小口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八。光绪四年,户七千一百四十九内,大口一万五千一百六十九,小口八千一百八十四。”[[17]]至光绪十年,隰州户口仍不及光绪元年的半数。以辽州为例,“通计州旧民数七万六千二百余口,三四两年饿死、逃亡、鬻外民数四万九千一百余口”。[[18]]关于山西丁戊奇荒的研究,社会史、灾害史研究领域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19]]本文故以山西省若干州县的地方志为文本,考察地方志中的“人相食”一语的书写规律及其功能、意义。
在书写模式上,正史所擅长的“《春秋》笔法”在地方志中也被延续。对前朝的“人相食”,地方志的作者们常常在“大事记”或“祥异志”中明确记载,这种处理方案与正史在“本纪”与“五行志”、“天文志”中记载“人相食”相类似。如光绪年间编修的《交城县志》“天文志”载:“(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大饥,人相食。”[[20]]民国时期编修的《介休县志》“大事谱”载:“光绪三年四月大祲,饿殍蔽路,人相食,有父子夫妻自相食者。”[[21]]民国时期编修的《太古县志》“年纪”载:“(光绪三年)岁大饥,人相食。”[[22]]即使是民国编修或增补的地方志,仍然重申了赋予“人相食”话语以“敬天恤民”之警示功能的“灾异”观念。经历丁戊大祲的辽州候选训导温显名认为,饥荒之际,乱象丛生,“鬻产不值一文,已被渔利者分其半,买粮不盈一掬,又为剽劫者夺之空,时势险危,人心焦灼。岂彼苍之眷顾不周 实斯民之罪孽难逭。所以戾气感召,奇灾流行”。[[23]]作为“灾异”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将饥荒归因于县邑士庶人等德行、风俗的败坏。
地方志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人相食”景况的功能与意义可以从地方志所彰显的基层州县治理模式中显现——基层州县治理模式以应然与实然交织的叙事形式反映在地方志中。地方志本身即被赋予政治治理功能。历代基层文化精英书写的地方志序以不同的文辞组合反复申明了这一功能,如:“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各宪入境观风,首事咨询,凡以知民风,察士习,审土宜,而借以措诸政治也”;[[24]]“邑之有志乘,所以使疆域沿革、户口盛衰以及士习民风、名流治迹、忠孝节义之气、衣冠文物之遗足以昭示来茲、信今而传后也”。[[25]]风,《玉篇》:“教也”;俗,《正韵》:“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在传统中国,“风俗”是基层治理的门径和晴雨表,“采风问俗”、“移风易俗”是亲民官的基本素养和理念,注重发挥地方志及其编修的“采风问俗”、“移风易俗”的治理功能,成为亲民官的基础性施政思路。
对于那些距离编修不太久远前出现了“人相食”饥荒的州县的地方志而言,应对饥荒与“人相食”困境成为整本志书的一个核心主题。在这些地方志的“建置”、“政略”、“人物”等门类,“大祲”一词频频出现。与正史相比,地方志叙述官民如何应对饥荒与“人相食”困境的视野,显得更为微观、基层。这些地方志文本中存在着一个以包含“人相食”景况的大饥荒为焦点的叙事格局。这种叙事格局的根源,在于地方志与正史一道被赋予“政典”的功能——尽管两者位阶不同。在地方志中,“人相食”一语也具有“政典术语”的属性。
地方志常常载明亲民官们在荒政方面的作为,如为民请命、争取惠政,组织绅商、多方赈济。一些恪尽职守的州县官员被表彰,用来“彰节烈而励官箴”。[[26]]如《介休县志》“名宦录”载:“巫慧,甫下车,值岁大旱,斗米千钱,穷民食草木,形多骨立。适运河南陕州米三万五千石过境,公截留,请于上官移知河南,两行省壮其胆识,俱允焉。因得减价平粜,民全活以万计。”[[27]]一些应对不力的亲民官在地方志中受到贬抑。如《沁源县志》“大事考”中,详述了光绪三年沁源令贻误赈灾时机、“下情壅于上闻”以及赈灾不力的过程,致使“(光绪)五年,大祲后,人烟稀少,豺狼横行。”[[28]]
地方志给予民间人物大篇幅的褒扬笔墨。地方志中的人物志记载了“人相食”之际表现优异的民间人物。这种褒扬是朝廷的“旌表”法规的执行。地方志的书写成为一种树立庶民效法的典范、向庶民宣示正当的行为模式的治理手段。在民国二十二年增补印行的《临汾县志》中,收录了丁戊大祲中的诸多典范人物,这些典范人物里,“孝友”7人,大体为农、商,其中饿死2人;“义行”14人,习儒业者有8人,饿死2人为务农者;妇女中的“节烈”、“孝友”、“义行”均归在“列女”部分,计20人,其中饿死12人,占收录相关人物饿死总数的近九成。这些人物的行为类型,包括舍身保全名节、舍己保全双亲、恪守夫妻兄弟信义、周济亲族乡邻贫人等等。地方人物志叙事的一个共同价值取向,是尊崇在困境中坚守儒家的共同体伦理准则。艾志端认为,地方志是“儒家修辞”、“儒家道德剧本”;而现实是,“灾难中成年女子与她们的男性参照物生活得一样,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更好”;“选择自杀或饿死而不是利用自身市场价值的年轻妇女,在死后被赋予巨大的道德价值。在当地知识分子眼中,那些利用自身市场价值、通过允许家庭成员出售她们或卖身来换取实物的妇女,丧失了所有的道德价值,却在很多时候从饥荒中存活下来了”。[[29]]
在地方志中,“儒家修辞”、“儒家道德剧本”不是唯一的话语和叙事类型,这类话语和叙事未能掩盖传统基层治理模式面对大饥荒时的困境。
其一,地方志揭示了饥荒之际社会秩序的蜕变轨迹。光绪六年,辽州士绅王基正作《辽州荒年记》,详述了饥荒之际米价的变迁和社会秩序的日渐崩解:“十数日,州南城外,路劫驼面数包。自是之后,道途之间有劫米面者、有劫钱物者,渐至有得财殒命者纷纷不绝”;“九月大饥,乡村无赖者多入室抢掠”;“街市鬻食买食者多被抢夺”;“自冬以迄戊寅春,数月之间,始而鬻物,继而鬻人,北直贩人贩物之夫遍城乡”;“穷乡僻壤、孤庙山庄之间,多被盗制命,甚有啖其肉而爨其骨者”;“至人畜食其肉、白骨露于天,伤心惨目,城乡皆是”;“州大祲后,盗贼公行”。[[30]]
其二,地方志揭示了饥荒之际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力量。魏丕信在一项以1743–1744年的直隶赈灾为中心的研究中指出:在清代盛期,朝廷的官僚制在饥荒控制方面起着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18世纪的集权官僚政府能够集聚和利用如此大量的资源,并能够进行粮食和资金的区际调运,这使其有可能独力承担起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救灾活动。”[[31]]从地方志来看,晚清的地方基层治理格局中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民间力量和外来力量,这些力量在丁戊大祲中比较活跃。在人物志中,除了扎根本土的传统乡绅、士绅之外,还可见那些行走外地的“商绅”作为商帮反哺桑梓的作为。作为外来力量的教士李提摩太、李修善的赈济活动在地方志中也有正面记载。这些力量,前者是本土生成的,后者是伴随西力东渐而来的,它们的活跃皆已构成对传统基层治理模式的冲击。
三、中国古代思想史脉络中的“人相食”话语和观念
《诗经》中有专门描写饥荒的篇章:“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32]]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脉络中,“人相食”是一个被思想家们不断思考、辩论的特殊世相——尤其集中在周秦之际与明清之交的变局时代。
“人相食”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蕴义的世相和固定表述,首先在作为思想史事件的儒墨论战中确立。在墨子的陈述中,常常可见当时的器物、食货、风俗、习惯、劳作等生活样式,如社会学、人类学素材。“昔者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33]]墨子开启了战国诸子对“利”这一范畴的争论和深究。在关于“利”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儒墨相攻最急。《孟子》的开篇,孟子与梁惠王对话的主题即为“利”:“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34]]墨子反复论说的主题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认为“利民”是“王天下”、“正诸侯”的要害,但这思路在儒家看来正是孟子开宗明义批判的汲汲言利的思路。孟子痛心疾首地宣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35]]在孟子看来,墨家着眼于“利”的学说的推行,必将至于“人将相食”的境地。正是在与墨家的论战中,在“人相食”话语和叙事中,孟子奠定了儒家心性之学的根基。
“食人”是孟子屡次谈论的话题,在开篇《梁惠王章句上》中即已出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36]]孟子指出为政者有责任使民众免于饥荒,如果府库中肥肉肥马充斥而民众罹于饥馑,则可称为“率兽而食人”。孟子批判了法家的耕战主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37]]孟子指出为政者有责任使民众免于战乱,而商鞅等法家之扩张导向的为政之道,在孟子看来可称为“率土地而食人”。孟子认为“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孟子》中,“人相食”尚未被作为现实描述,但孟子认为“人相食”在“仁义充塞”之后必将出现,其机理在于杨墨之道的传播“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影响了个体的行为模式和为政者的施政模式。《庄子》也曾以预言的口吻声称:“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38]]
一场现实发生的“人相食”受到举国君臣的关注和议论。安史之乱中,睢阳攻守战极为惨烈。张巡、许远坚守待援,城中粮尽后,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后晋刘昫等撰的《旧唐书》中,将二人列入“忠义传”,在叙及张巡杀妾飨卒之后,记载了张巡以民为食的情节:“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39]]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中,二人亦入“忠义传”,但叙及张巡杀妾、许远杀奴仆以飨士卒后,仅记“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40]]并无杀民以食情节。而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载:“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捕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41]]
《资治通鉴》专门记载了李亨登基后论功行赏时关于张巡“食人”的争论:
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为之作传,表上之,以为:“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瑕弃用,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也,以待诸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荣禄。若不时纪录,恐远而不传,使巡生死不遇,诚可悲焉。臣敢撰一卷献上,乞编列史官。”众议由是始息。[[42]]
张巡、许远守城战中的“食人”之举受到指责,是儒家“人相食”话语的历史影响力的表现。李翰的辩护,强调张巡此举在主观上出于“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且“乖其素志”,客观上“以寡击众,以弱制强”而且最终“死大难”。李翰运用虚拟语气推论,即便张巡守城时在主观上已有“食人之心”,但客观上起到了“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的伟大功绩,亦可功过相抵。李翰所称“损数百之众”与《旧唐书》中“所食人口二三万”相去甚远。
韩愈与张巡的下属有深交,对张巡的“食人”亦持宽容态度,赞许其“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43]]而忽略了以民为食的情节。与此态度相异的是,一些州县旌表割股疗亲者并为之免赋,韩愈对此持明确的批判立场:“母疾则止于烹粉药石以为是,未闻毁伤支体以为养,在教未闻有如此者。苟不伤于义,则圣贤当先众而为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则毁伤灭绝之罪有归矣。”[[44]]
通过对此事件的讨论及史书叙事,恪守君权至上的“忠义”价值目标成为减轻“人相食”的罪责的理由,这一理由亦成为“人相食”话语在历史变迁中沉淀形成的观念类型之一。
明清易代之际,因饥荒与兵祸而发生的“人相食”在正史中频繁出现。作为同时代者,顾炎武与王夫之均就“人相食”景况作了深刻论说,将中国传统中的“人相食”话语及其蕴义提升至新的高度。
顾炎武发展了孟子的“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观点,主张“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45]]在指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意味着“亡天下”之后,顾炎武提出“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王夫之对“人相食”的论述较丰。王夫之批判朱熹将《孟子》所论“人将相食”作为譬喻的观点。“‘率兽食人,人将相食’,《集注》作譬喻说。看来,孟子从大本大原上推出,迎头差一线,则其后之差遂相千万里,如罗盘走了字向一般。立教之始,才带些禽兽气,则习之所成,其流无极;天下之率兽食人者,亦从此生来;天下之人相食也,亦从此生。祸必见于行事,非但喻也。”[[46]]
王夫之认为,杨朱、墨子的学说,以及佛家的学说,在论说的逻辑上,均能推论出“人相食”的合理化。“如但为我,则凡可以利己者,更不论人。但兼爱,则禽兽与人,亦又何别!释氏投崖饲虎,也只是兼爱所误。而取人之食以食禽兽,使民饿死,复何择焉!又其甚者,则苟可为我,虽人亦可食;苟视亲疏、人物了无分别,则草木可食,禽兽可食,人亦可食矣。”[[47]]
尽管历数杨墨与佛家学说与“人相食”的关联,但王夫之对臧洪为“义”杀妾、张巡为“忠”杀妾并食民的行为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对臧洪出于“士为知己者死”的行为,王夫之的评价是:“洪以私恩为一曲之义,奋不顾身,而一郡之生齿为之倂命,殆所谓任侠者欤!于义未也,而食人之罪,不可逭矣”;“其愤兴而憯毒,至不仁而何义之足云 ”[[48]]“在王夫之看来,义是从属于仁的,臧洪的行为既不仁,也就谈不上义,不但不应予以表彰,且当‘正其罪而诛之’。”[[49]]
王夫之对张巡杀妾并食民的评价,恰是与八百年后对李翰为张巡辩护的针锋相对的回应。或者说,李翰平息争执的“宏论”,在八百年后等到了一个颠覆性的反击:“夫人之不忍食人也,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也,固闻言而心悸,遥想而神惊矣。于此而忍焉,则必非人而后可。巡亦幸而城陷身死,与所食者而俱亡耳;如使食人之后,救且至,城且全,论功行赏,尊位重禄不得而辞,紫衣金佩,赫奕显荣,于斯时也,念啮筋噬骨之惨,又将何地以自容哉!”;“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50]]与李翰的论说一样,王夫之也运用了虚拟语气,假设张巡在食人之后救兵到来、功成荣显,将何以自处。“天下至不仁之事,其始为之者,未必不托于义以生其安忍之心”;“浸及末世,凶岁之顽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啮而心不戚,而人之视蛇蛙也无以异,又何有于君臣之分义哉 ”[[51]]王夫之认为,天下最为不仁的行为,也会以“义”为托辞,由此滋生安忍之心,而终至于父子、兄弟、夫妻相食而心无忧伤,“分”与“义”荡然无存。
章学诚云:“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52]]至此,滥觞于六经的中国传统中的“人相食”话语不绝如缕,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思想史上的一个有着特定内涵与功能的固有表述。以人类对“人相食”的怵惕哀矜的基本情感为起点,视其为常态化的规则、秩序与正义崩溃的表征,引发对执政者施政过程与绩效的批判检讨,强调政经文化精英乃至天下普通个体在世乱之际的责任担当,是这个话语系统的主流蕴义。
然而中国古代思想史有着复杂的格局和层次,并非有着标准件般规范意识的“铁板一块”。这个特点在“人相食”话语系统中亦有体现。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思想史素材中,也存在着旗帜鲜明地论证人相食现象合理性的文字,但是这些文字与叙事中,皆无“人相食”这一短语。或者说,这些文字的作者,通常是在避开这一固有表述的前提下展开论说。
如晋人杨泉作《物理论》,其中论曰:“汉末有管秋阳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则三人俱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孔文举(孔融)曰:‘管秋阳爱先人遗体,食伴无嫌也。……此伴非会友也。若管仲啖鲍叔,贡禹食王阳,此则不可。向所杀者,犹鸟兽而能言耳;今有犬啮一狸,狸啮一鹦鹉,何足怪也 昔重耳恋齐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师而欲食伍参;贤哲之忿,犹欲啖人,而况遭穷者乎 ’”[[53]]另外,《金楼子·立言》篇中记孔融语:“三人同行,两人聪俊,一人底下;饥年无食,谓宜食底下者,譬犹篜一猩猩、煮一鹦鹉耳。”钱钟书先生认为:“并举猩猩与鹦鹉者,用《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底下者’当为‘聪俊者’食,犹《吕氏春秋·长利》篇记戎夷与弟子野宿寒甚,谓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衣之与食,殊事一致。”[[54]]这几则文字的共同点,是在认可“人相食”可行性的前提下,权衡得失损益,讨论何种食法更加合理,颇有经济学成本效益计算的兴味,也恰与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气质、致思风格相合。
与前述论说相呼应的是,从正史和野史的描述来看,认可“人相食”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讨论何种食法的思想方式有着鲜活的具体实践。如“易子而食”,即为最早上书的食人方案;又如张巡的食妾、许远的食奴仆,先食城中妇人,继以男子老弱,在这些方案中,亲疏、身份、强弱等成为食人的秩序依据。笔记小说记载,南宋时,“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老瘦男子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55]]在这些食人方案中,先前的亲疏、身份、强弱标准已显得迂阔,而采取笼统的分类命名法,将人肉贴上非人的标签,以求得安忍之心。
在一个常态化规则、秩序已经崩溃的场域中,竟在食人的实践中生成了一种非常态的规则与秩序。而且,后一秩序与前一秩序之间的内在机理有相通之处,如身份差序格局的作用、“正名”论的影响。在两种规则与秩序中,后一规则与秩序,是没有德性根基的规则与秩序,如王夫之所言,“至不仁而何义之足云 ”不仁之义、无仁之义,即为伪义。在儒家讨论“人相食”的话语系统中,“仁”被赋予规则、秩序与正义的根基的属性。
结语:“人相食”在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非司法化
在“洞穴奇案”的讨论中,案情并没有被化约为“食人”问题。“‘食人’一词最先出现在欧洲语言里,是当哥伦布用它来指安德利斯群岛加勒比人被他的阿拉瓦克人向导描述为吃人肉的好战分子。从那时开始,它传入了西班牙语,然后进入到其他语言当中,在欧洲人和他们看做野蛮或劣等人之间,短语‘食人主义(Cannibalism)’与殖民遭遇紧密联系。”[[56]]本文起首由“洞穴奇案”的吃人情节联想到“人相食”短语,本身即为以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审视该案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洞穴探险”的想象,成为经典的有《枕中记》、《桃花源记》之类,其皆着眼于向往某种比现世更美好的生活样式。富勒的洞穴探险者系富有闲暇的精英,结为组织团体,以“冒险”、“科学”为鹄的,这为案件的当事人预设了个体主义的现代性背景。以中国古代的司法体系与司法技术,如循吏模式、酷吏模式或“《春秋》决狱”、“服制定罪”、“情理”司法、“抵命”观念、“海瑞定理”[[57]]之类,裁判现代性背景下的“洞穴奇案”,虽有方柄圆凿、鸡同鸭讲的嫌疑,也可作出数量不少、面目各异的判决。在《洞穴奇案》一书所列的裁判依据中,也仍然可以找到中西与古今之间相契相应的思想方式、致思风格,例如珍视共同体的德性根基的思路,或者孜孜于个体得失计算的思路。
既然“人相食”在中国古代频繁发生,那么中国古代司法对此如何处理 我们发现,在中国古代史的范围内,很难找到“人相食”作为个案进入司法程序的史料。“人相食”的非司法化,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一个规律。“人相食”非司法化的基础之一,是讲求“缓刑”的荒政传统。历代的荒政书教导官吏们如何应对灾荒。在列明的良策中,“缓刑”的条目靠前。“缓刑”被认为具有“上干天和”的感应功能,要求亲民官们对民众迫于饥寒而犯禁的行为,深加体恤与哀矜。在应对“人相食”挑战法律体系的过程中,“缓刑”既是一种美好的宏大理念和修辞,又是一种实用的施政原则和举措。“人相食”的非司法化,又与“人相食”具有的政治意义有关。以官僚系统操作技术观之,若纯以法条为裁判依据,“人相食”的个案大多为“命案”,按照命案审理程序,这些案件将进入复核环节,上呈至皇帝,这种局面既彰显了地方官治理的失败,又表明了君主治理的失败。
在中国法律传统中,“人相食”话语和观念的力量,表明了作为“类”与“群”而存在的“人”的地位和力量,这种地位和力量有谶纬观念的支持;与此相比,权利关系主体意义上的个体之“人”的地位和力量却是脆弱的,这是中国古代史中的“人相食”话语和叙事的一个内在逻辑。另外,儒家强调规则与秩序的德性根基,如王夫之所言:“至不仁而何义之足云 ”以怵惕哀矜的人类基本情感为原点的“仁”具有规则、秩序与正义的根基属性,这是从儒家“人相食”话语系统中呈现的一个本土政治法律命题。
[[1]] 参见[美]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2]] 《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第一》。
[[3]] 杨联陞:《二十四史名称试解》,载《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4]] 《旧五代史·卷一百九·列传第六》。
[[5]] 《新五代史·卷三十九·杂传第二十七》。
[[6]] 《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第一》。
[[7]] 这一名句的“母题”,是王莽篡政后某次朝议时校尉韩威请求击退匈奴的进言:“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参见《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8]] 《晋书·卷一百十五·载记第十五》。
[[9]] 《三国志·魏书·卷七·传第七》。
[[10]]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一十七》。
[[11]] 《新五代史·卷五十二·杂传第四十》。
[[12]] 《明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十二》。
[[13]] 《明史·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八十四》。
[[14]] 《新唐书·卷七十五·列传第十二》。
[[15]]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杂传第三十五》。
[[16]]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页。
[[17]] 光绪二十四年《续修隰州志》,卷二,户口。
[[18]] 三十八年《辽州志》,卷六,续艺文,记。
[[19]] 代表作如[美]艾志端:《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曹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郝平:《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0]] 光绪八年《交城县志》,卷一,天文。
[[21]] 民国十九年《介休县志》,谱第二,大事谱,卷三。
[[22]] 民国二十年《太谷县志》卷一,年纪。
[[23]] 民国三十八年《辽州志》,卷六,续艺文,记。
[[24]] 光绪六年《蒲县志》旧序,湖必藩撰。
[[25]] 道光二十三年《阳曲县志》序。
[[26]] (清)高枬:《高枬日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17页。
[[27]] 民国十九年《介休县志》,录第五,名宦录,卷十八。
[[28]] 民国二十二年《沁源县志》,卷六,大事考。
[[29]] [美]艾志端:《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曹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217页。
[[30]] 民国三十八年《辽州志》,卷六,续艺文。
[[31]] [法]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32]] 《诗经·小雅·苕之华》。
[[33]] 《墨子·节葬下》。
[[34]] 《孟子·梁惠王上》。
[[35]] 《孟子·滕文公下》。
[[36]]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37]] 《孟子·离娄章句上》。
[[38]] 《庄子·杂篇·庚桑楚》。
[[39]]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列传第一百三十七下》。
[[40]]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一十七下》。
[[41]]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
[[42]]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
[[43]] 《韩愈文集·文集卷二·张中丞传后叙》。
[[44]] 《韩愈文集·文外集卷上·鄠人对》。
[[45]]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正始》。
[[46]] (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孟子·滕文公下篇》。
[[47]] 同上注。
[[48]]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
[[49]] 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9页。
[[50]]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三。
[[51]]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
[[52]]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53]] 《意林》卷五引杨泉《物理论》。
[[54]] 钱钟书:《管锥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2~720页。
[[55]] (宋)庄绰《鸡肋编》。
[[56]] [美]艾志端:《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曹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57]] 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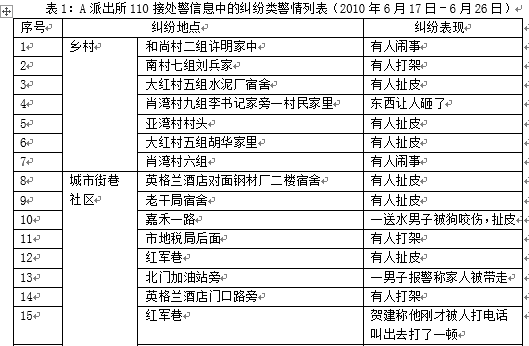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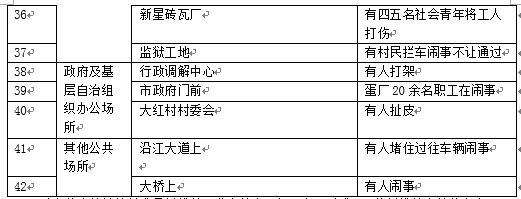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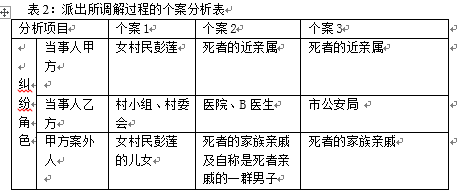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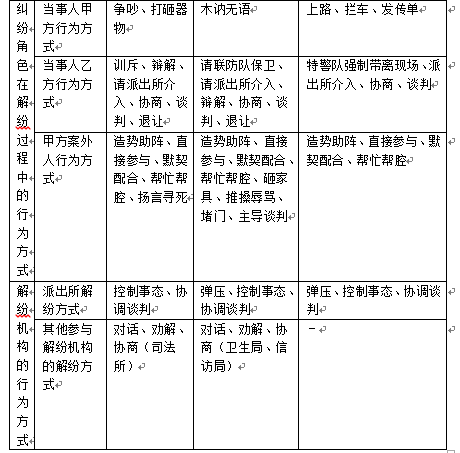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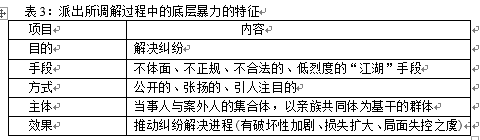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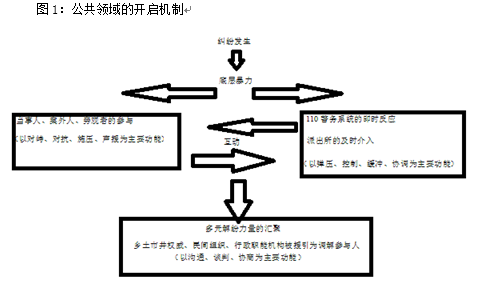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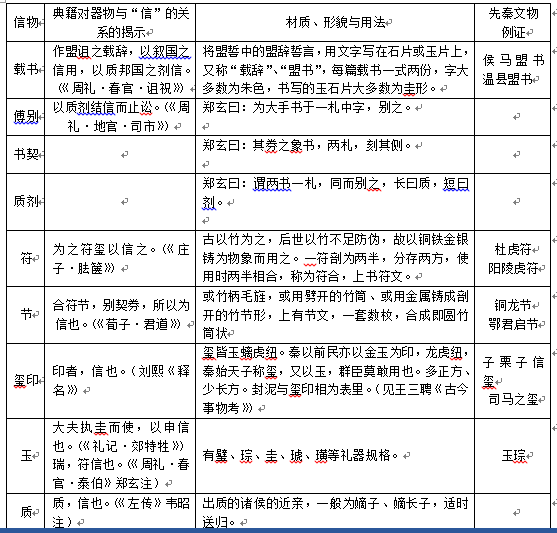
.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