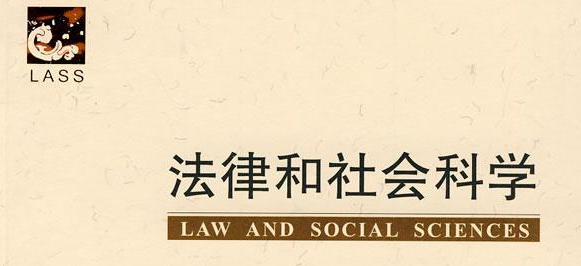作者王启梁,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问题: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到来
二、简单案件如何演变为“难办案件”
(一)新媒体的后果:再没了“天高皇帝远”
(二)官民舆论战:法律观的分歧
(三)孤立的高院:司法中的政治
(四)骑虎难下:非典型“难办案件”
三、并非中国特色:民众舆论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一)司法公信力:单维还是多维
(二)量刑改革的努力:弥合公众与司法系统之间的分歧
(三)究竟谁能影响司法:被忽略的政治
四、讨论:建构法律沟通的理性之路
(一)司法引领社会变革:先找到钥匙
(二)在事件流中交战并辨识法律的社会意义
(发表于《法学家》2012年第3期)
一、问题:法律世界观紊乱时代的到来
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奸杀同村19岁少女王家飞、摔死王家飞3岁的弟弟王家红。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昌奎随即提起上诉。二审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于2011年3月4日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李昌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直到2011年5月16日(王家飞姐弟被害两周年)被害人亲属到看守所了解李昌奎执的死刑行执行时间才知道案件被改判了。2012年5月中下旬开始,受害人亲属开通微博、上网发帖并赴昆明上访。6月中下旬此案成为万民关注的轰动案件,并引发官民激辩。其间云南省高院有关人士发表被民众称为“标杆论”的言论(详见后文),引发舆论怒潮。迅即,云南省高院于7月16日做出再审决定,于8月22日再审改判李昌奎死刑。此案进展经历曲折、舆论沸腾。
笔者以云南网、凤凰网、腾讯网、雅虎等媒体的资讯为基础,[1]简要整理了李昌奎案件的进程中的主要焦点和不同观点、立场,见下表:
李昌奎案件主要争论
| 争议 | 云南省高院 | 民众 | 受害人亲属 | 李昌奎及其亲属 | 学者/专家 |
| 李昌奎改判死缓是否合法、合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 2011年7月4日,云南高院认为改判合法、合理;“标杆论”;决定再审 | 7月5日晚,腾讯网显示97.78%的网友认为二审改判量刑过轻;鹦哥村民联名上书反对二审结果。 | 愤怒;不解。 | 对改判均感非常意外;李昌奎非常珍惜这一机会,在看守所劳动表现非常积极。 | 多数观点1:法院改判不恰当,例如阮齐林教授、王琳副教授。少数观点2:改判合理合法,例如邵国恒律师。 |
| 对云南高院再审的看法(关于法律权威性、稳定性的争论) | 有法官认为伤害了司法权威 | 多数观点:符合正义 | 应该 | 非常不解;李昌奎很绝望 | 观点1:应该,错案可纠,如何兵教授;观点2:不该,伤害司法独立和权威,如贾谊教授;观点3:应该,但不应由云南高院启动,如游伟教授。 |
| 该案是否民意绑架司法 |
|
|
|
|
|
(关于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的争论)
| 有法官认为是 | 民意无错 | 感谢民众呼声 | 不明 | 观点1:不是,如高铭暄教授;观点2:是,如沈彬评论人;观点3:没有民意监督,司法可能更加不公,司法成为独裁。 |
从对这些最为基本的问题的立场可以看出,法官、民众、学者、法律职业者、受害人亲属、罪犯对这一案件的二审和演变充满了相互冲突的分歧。李昌奎案与许霆案、梁丽案等不同,[2]它不属于法律适用上的疑难案件;也与刘涌案不同,[3]对李昌奎犯罪事实的确认不存在程序违法或证据瑕疵,法律事实非常清楚。它不是疑难案件,却代表一类案情不复杂、法理不艰深、法律适用不困难却又难办的“简单案件”。笔者所要探讨的不仅是公众舆论、受害人亲属与云南省高院的判决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重大分歧,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出现这些分歧 并且还要借助“事件-过程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民意是如何被呈现的,[4]以及这一案件里处于关系格局中不同位置的被害人亲属、媒体、民众、法院、检察院、法学家等是如何互动和隔绝的,一起“简单案件”如何演变成“难办案件”。这一写作中,笔者还试图运用人类学的视角把事件进展中的话语和不同角色的法律表达作为田野资料加以“深描”式的分析、解释,以挖掘行动背后的意义。[5]
首先,文章将表明,法律的实践从来未曾脱离过它所存在的时代和社会,法律现象常常作为时代和社会的病症表现出来——现代社会的到来并没有增加人们的稳定感和确定性,相反,变化和不安始终是现代性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再终老是乡,空间的转移带来了社会关系的类型、性质的多重化和立体化,人们在乡土社会性质的熟悉感和陌生人关系的疏离感中往来穿行。[6]更重要和令人沮丧的是,人们不断地被扑面而来的多样性——不同世界、经验、观念、法律所袭击和包围,一切曾经看起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成为了冲突的来源,曾经牢固的信念犹如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房屋。法律和法律的实践并非冷漠的条文和典章,它的背后有着世界观的指导,它来自于人们关于何为正义、何为正确的行为、生活方式的界定与践行,是一套意义和分类的体系,[7]因此,它被称为“地方性知识”。[8]然而,在人口高度流动、媒体高度发达以及所谓全球化与地方化的遭遇中,来自不同世界和社会的观念不断地在庞大的社会体系中被传播和交锋,法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的体系均受到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冲击。不同的法律经验和正义观念让人们发现,在多元性的法律观中,任何一种“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观都不再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些多元的法律观之间的竞争和辩论使大部分人感到茫然无措而又积极投身其中。人们必须在辩论中方能确知何为正义,那种来自于乡间或传统的共识在现代性到来之际似乎开始失去了立足之地,因为,最简单的正义信条和正义的感觉也会受到质疑和动摇——并且这些质疑和动摇同时来自于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这表明,人们处在一个多元的法律世界观之中,尤为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它们之间无法融贯或者使之融贯的代价高昂。这是一个变化、流动的时代,法律的多元世界观紊乱仅只是时代特征在法律世界中的折射。因此,有人说“现代性特有的不确定性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9] 李昌奎案件的演变过程彰显的正是这种世界观的紊乱、冲突以及不确定性。
“世界观”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被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和阐发。[10]方乐在文章中把世界观定义为:“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内部认知的知识交融。”[11]这一见解侧重于知识论,而笔者更想说明的是法律世界观与制度安排、行动包括法律实践、对法律的评价的关联性。人们的法律世界观与更高的世界观即哲学上所说的对世界的概念相联系,它是关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何为正义和正确的生活方式的认识和理解在有关法律事务中的反映,并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规范行为)、法律实践或评价法律现象的行动指南及认知框架。法律世界观是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一套意义和价值的体系。法律世界观来自于人们的日常实践、社会化——这往往是普通民众的法律世界观形成的方式,也会来自于精心的学习和司法实践——这往往是针对法律精英,当然,并不意味着所谓法律精英的法律世界观的形成会脱离日常生活的影响。在传统的小型社会中,法律世界观往往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人们共识程度高,决定着人们对秩序安排的倾向,并塑造出规范性的生活,例如对环境的依赖与保护。[12]现代性的到来则破坏了社会群体的自足性和世界观的整体性(这并非说小规模社会就不会有世界观的紊乱),每个人都被迫面对多样性的世界观。但是,法律实践中的麻烦不是因为不同群体会具有不同的法律世界观,关键在于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是否表达了整体性的法律世界观并能大致被民众所接受,以及多样化的法律世界观之间是否能够融贯。法律世界观决定了人们对法律事件是否有最基本的的共识,而是否有合适的沟通方式和渠道决定着当分歧发生时不同的法律世界观之间能否相互沟通并最终融贯、兼容。[13]
李昌奎案件的演变说明,一方面,由于缺乏整体性的法律世界观,以至于人们尤其司法界内部就“简单案件”都无法达成基本的共识;另一方面,因为缺乏使不同法律世界观得以融贯的途径,导致分歧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反而制造出更多的不确定性。
其次,面对李昌奎这样一起非典型意义的难办案件,民众更多的是批评云南省高院在二审中量刑不当,由此引发了关于是否应该废除死刑的讨论,以及再审是否伤及司法权威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笔者想强调,李昌奎案件并非一个孤立的个案,它是一起以法律问题呈现出来的事件;也不属于刑事案件中常见的量刑失当,它的出现不是偶然。如果按照宾凯对卢曼系统理论的研究,“把法院定位为一种决策组织”,[14]那么,我认为至少今天的中国法院并不是一个闭合的系统,相反,它向某些方面开放而非自足。并且,它虽是决策组织,却有着司法及司法之外的多种决策同时发生于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法院和案件背后有许多类似于福柯意义上的“隐秘”,或许这些隐秘就是可以被称为“政治”的东西——才真正支配着案件决策的运作。[15]
最后,仅仅认识到这是一个法律世界观紊乱或者说一个多元法律世界观相互交战的时代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追问司法能否、如何引领社会变革 司法者如何建构其健全的司法理念 法律的社会意义又是如何形成的 不同的法律观如何能够获得融贯 这些问题关系着我们将何去何从。
二、简单案件如何演变为“难办案件”
在此部分,笔者将以事件的过程为线索,检讨这一案件是如何从简单案件最终演变为难办案件的 在这一过程中,哪些现象值得重视 哪些问题值得检讨
(一)新媒体的后果:再没了“天高皇帝远”
李昌奎案件的发生地昭通市巧家县处于云南北部,当事人所在鹦哥村放牛坪社则更远,位于金沙江边的大山深处,从村里需走2小时的山路,再坐3小时公交车才能到县城,无疑是一个边远的地方。空间的阻隔的确造成了受害人亲属了解、参与和影响案件进程的巨大困难,这从他们千里迢迢来到昆明艰难申诉可以看出。[16]然而,事情却出现了转机。受害人的哥哥于2011年5月17日首先在腾讯网上开通微博传播案情,[17]随后开始在各大论坛发帖,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新闻报道和网络舆论,使李昌奎案昭然天下,最终扭转了检法两家的漠然姿态,对申诉做了回应,表示将审查此案。[18]此后才有了再审。在整个过程中,受害人亲属无疑使用了恰当的策略,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兴起,受害人亲属的上访不知还将持续多长时间。
可以想象,如果这起案件发生在十几年前,在没有网络、微博、博客、QQ的年代,你我得知案件信息的时间可能要推迟几个月、几年甚至永远无法得知。而李昌奎事件从2011年3月4日二审判决以后,在短短的5个多月就发生了一连串戏剧性的变化。李昌奎案充分地说明了一个极为简单却至关重要的问题:地理空间造成的信息阻隔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所消解,“天高皇帝远”已经成为过去,发生在边疆的事件完全可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变得相对化。
任何民意的发动、呈现都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民意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力将有所不同。李昌奎事件再次说明,“在互联网的世界中,人们的互动关系不再依赖于时空的一致性,社会关系的建构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网络的公共空间化使网络民意摆脱了地域化的限制,使‘不在场’的、素昧平生并可能永远不会有直接接触的人们在即时形成民意。”[19]社会条件决定了法律实践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的司法系统似乎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信息和舆论发生方式的转变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威力,或者虽然认识到却没有形成有效的应对措施、以更加审慎的方式对待审判可能带来的风险。
(二)官民舆论战:法律观的分歧
如果说新媒体的出现使信息的迅速传播成为了可能,但是舆论的形成却取决于事件本身是否具有新闻和舆论价值。比起众多的凶杀案件,李昌奎的凶杀情节、作案动机等算不上非常有“卖点”,并不是很能满足公众对冲突、悬念故事的兴趣。[20]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李昌奎案与此前发生的药家鑫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另一方面,回顾这一事件的进程,从民众的反应和社会舆论来看,云南省高院的回应方式、话语极大地挑战了民众最基本的公正感、刺激了民众的神经,使这一事件的新闻价值大增。
受害人亲属得知二审结果后展开了申诉,“向省检察院申请,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提起抗诉,撤销终审判决。也向省高院提出申诉,希望省高院启动再审程序,改判死刑。‘我们向省委政法委,甚至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都递交了申请书,不过到现在都没有回音。’”[21]直到7月5日云南省高院新闻中心相关人员才表示:“省高院对此事非常重视,目前已经派专人对此案进行重新审查,之后会向社会公布一个审查结果。至于是否会提请再审程序等等更多情况,目前还不便透露。”[22]接着,7月6日云南省高院有关负责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李昌奎案件改判答疑,大体意见是:第一,改判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现;第二,高院判决程序合法,不存在徇私舞弊;第三,李昌奎案属民间矛盾,社会危害相对较小;第三,民众的不解是由于“杀人偿命”传统与“少杀慎杀”理念有差异;第四,李昌奎有自首情节。[23]
云南省高院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但是以上辩护以及二审判决书中改判的主要依据均遭到民众和大部分法律专家的质疑。[24]二审改判之所以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应,与二审判决书的书写方式有极大关系。二审判决书的前半部分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书的通常写作并无差异,套路仍然是对作案过程的详细描述——这极易引发观者对犯罪者的人神共愤而使死刑判决获得认同。问题出在对李昌奎进行改判的几个重要事实(自首、积极赔偿、悔罪态度好)既无法理也无证据事实支撑。这必然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这相当于二审判决的前部分已经认定李昌奎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和证据来支持对他的宽大。这充分说明,针对容易引发社会争议的案件中,法院判决书的写作必须重视最基本的说理。
然而,最令人预想不到的情形还是发生了。7月12日云南省高院的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快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改判或者不改判,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能因为大家愤怒,就随意杀一个人,法院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民众、媒体、学界。但最终,审判还是要以国家的法律为基准”。应该说,这一言论还是较为客观和能够被接受的。可是,这一采访中还同时出现了以下被社会大众称为“标杆论”、“狂欢论”的言论:
“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这是一个宣泄情绪的社会,但这样的情绪对于国家法律而言,应冷静。我们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轻易草率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
“10年之后再看这个案子,也许很多人就会有新的想法。”“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
之所以采取死缓,也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有明确规定: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
为什么最高法近年来一直提出“少杀”、“慎杀”,就是要给予人性和人权。“我们不能再冷漠了,不能像曾经那样,草率判处死刑,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要改改了。”
减少死刑已经成了大趋势,现阶段我们不能再用酷刑,这是奴隶制、封建制的落后方法……[25]
前一阶段,省高院法官做的是释法,试图从法律的专业性角度为二审的改判进行辩护,虽然正确与否、是否被接受是另一回事,但毕竟还在案件的框架内即如何适用法律。正如台湾学者李佳玟教授指出的:“由于死刑是国家法定刑,裁判者在每一个具体个案里,只须就选择死刑之具体情况进行说明,不必(或许也无意)提供死刑制度存在的正当性。”[26]然而,“标杆轮”及后文将涉及到的匿名法官在《南方周末》的文章则大大超出了法律适用的问题,它直接指向的是死刑的(不)正当性问题,并且以权威的方式直接否认了民众关于对残忍凶杀的公开谴责,以及社会有能力对抗恶行的决心。[27]从社会心理来讲,这暗示了药家鑫案的判决是错误的。这种修辞超出了人们的认知框架、朴素的正义观和讨论范围。“标杆轮”的另一个问题是它的道德性话语风格,这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被解读为对民众的野蛮化。如果说,人们愿意接受和参与对法律、司法解释的不同观点的辩论中去,那么对于以上言论,很容易被民众理解为精英的傲慢和挑衅,这是往已经深感判决不公的民众身上浇油点火。在整个过程中,云南省高院逐渐陷入被动,这种被动来自于二审的改判选择了一种严重违背民众朴素情感和公正观的方案,并且在此后的舆论交锋中使用了无法自圆其说的道德性修辞。
笔者并不认为这是法官的非理性行动和言辞,相反,法官们即使不是深思熟虑至少也认真准备过。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标杆论”之前的释法已经表明了部分法官的法律观与民众的法律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标杆论”则凸显出更大的差距。
(三)孤立的高院:司法中的政治
从7月5日面对媒体直到做出再审决定之后,云南省高院和部分媒体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程度上为二审改判进行了辩护。[28]然而,这些辩护大多受到有力的质疑。[29]云南省高院在这一过程中的言行带来了预想不到的社会反响,在官民间的舆论交战中,云南省高院与民众合力把自己不断推向舆论的巅峰。
就在云南省高院有关人员发表了“标杆论”之后短短几天,云南省高院随即于7月16日就做出再审决定。[30]我们有理由相信此前向媒体释法以及发表“标杆论”、“狂欢论”的法官并非擅自代表高院发言;也有理由相信“标杆论”、“狂欢论”的出现与个人言辞风格、个人的法律观表达有关,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云南省高院的官方立场。然而,对于民众来说,说话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代表了谁,民众不会也无需去区分个人风格与官方立场之间的细微而重要的差别,这符合常理。可以说,不当的言论、转折过快的立场导致云南省高院再审李昌奎案件时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这似乎可以说,是舆论逼着云南省高院骑上老虎而欲下不能。我们必须意识到,最初二审改判李昌奎案件的是云南省高院,而不是民众、舆论。关键问题在于,是什么促使云南省高院做出各种选择和行动呢 是什么促使该案件中法官表现出废除死刑的决绝主张呢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设置新的死刑复核制度本身是政治的一部分——国际人权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结合。这又最终成为了新的刑事司法政治。让我们暂时忽略那些关于废除死刑的辩论,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云南省高院要在二审中改判李昌奎死缓 联系起发生在云南以及不同地区出现的所谓的“赛家鑫”翻案风来看,[31]如果我们相信这不是司法腐败的结果,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李昌奎改判死缓不是偶然,其背后有着某种“隐秘”支配着死刑到死缓的改判。这种隐秘或许正是王琳所说的:
“根据当下的死刑复核制度,死刑立即执行的复核机关是最高法院,而死刑缓期执行的复核机关是高级法院。从死刑核准制度上分析,高院更多考量的也许是:如果维持中院的死刑立即执行,那就得报请最高法院核准。若将来被最高法院驳回或改判,必然影响二审判决的维持率(或改判率)。而在高院就改判死缓,则是由高院自己核准,完全无影响“政绩”的担忧。当然,人命关天,改判死缓在程序上也要受到诸多制约,它一定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死刑复核制度形成的生死距离,未必是促发高院更愿改判死缓的关键原因——但至少是其中之一。说不定还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32]
法官尤其是高级法官从来不是存在于政治之外的真空中。对于云南省法院系统来讲,由于毒品等案件高发,死刑控制一直压力巨大,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这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33]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把云南省高院逼到虎背上的其实是死刑核准率——这无疑是“压力型体制”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34]是司法系统的“指标化”运作。[35]虽然死刑复核率不同于破案率之类的刚性数字化指标,但是由于其能够对下级法院的判决作出否定性评价,仍然会产生出诱导性和约束性来。[36]云南省高院把李昌奎案件及其他与之相似的案件改判死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死刑复核控制的应对。
把云南省高院与最高人民法院控制死刑的关系考虑进来,尚不足以理解二审改判,因为作为个人的法官并不必然对最高人民法院负责。在云南省高院的回应中强调了“李昌奎案的判决是法院审委会全体委员集体过半数作出的”,然而一则评论中提供的信息似乎对于理解二审改判似乎更有所帮助:
“因为被告人李昌奎的家人‘救人无望’,甚至连律师都没请,更不可能去花钱找关系。案件进入审委会,也没有多少改判的声音,只是有人提出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发出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中有‘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的说法儿。基于这种‘区别’,审委会便将一审的死刑判决改为死缓。”[37]
如果以上说法属实,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最初大部分审委会成员并不认为一审有错误或不当;第二,之所以改判是审委会受到了某种影响并选择了从死刑核准率、留有余地(避免冤案)来讲对高院整体有利的方案。用一位律师的话讲“为了迎合‘少杀、慎杀’刑事司法政策,将罪大恶极的李昌奎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38]第三,审委会的成员也受制于某种结构性的约束。从这些情况看,死刑复核形成的巨大压力使法官们在二审的决策中已经不能只考虑司法,这个引起滔天舆论的二审结果事实上是一个政治和司法的双重决策结果。
此时,我们会进一步发现,“标杆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其背后恰恰是理性使然。无论是二审的改判、事后的释法或“标杆论”,其对话对象从来都不完全是民众和当事人,其主要对象是最高人民法院、是表达云南省在关于减少和废除死刑的立场,这才是认识云南省高院表面的错误释法以及不该有的高调的关键。“语言论述、说话方式以及各种语言运用的策略,在现代社会中,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并在当代社会的权力斗争、正当化程序、去分化以及社会结构重构中,发挥特殊的社会功能。”[39]改判李昌奎死缓与“标杆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政治和法律立场的象征性实践——关于废除死刑和“少杀、慎杀”的极端版本,都有明确而又不为外界所知的对话对象。
云南省高院的麻烦来自于,话语不能脱离其语境。当李昌奎案被公之于众之后,语境变了,话语被公开化了,对象也被具体化了。人们并不会考虑到云南省高院要面对最高人民法院,人们只会就省高院的释法、辩护与李昌奎案的具体案情联系起来;人们并不会考虑云南省是一个死刑大省,只会考虑李昌奎到底该不该杀。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在不同的听者听来其意义和社会效果会有巨大差异。或许,如果不是出现在李昌奎案件而是换一个案子,“标杆论”就成了政治正确,释法的法官反而会受到高度赞誉、成为推动废除死刑的斗士。
李昌奎案件演变成云南省高院不再能够完全掌控的一起事件,其原因就在于,受害人亲属、民众参与导致云南省高院所要面对的关系变化了。在二审改判之前,他们面对的是和上级法院的关系(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忽视的),二审改判主要是法院系统的内部关系使然。二审后的舆论风波导致云南省高院所处的关系变成了复杂的关系丛,不仅是上下级法院的关系,还包括了与社会大众、检察院以及其他没有公开化的力量的关系。这一点是云南省高院没有完全准备好的,这才导致释法和“标杆论”都显得不合时宜。
舆论爆发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行动也是耐人寻味的。从整个事态的发展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始终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和表态,这与当年的刘涌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40]我们无法揣测最高人民法院为何如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得以“保全”自己未被卷入这一骑虎难下的难办案件中,人们的批评声始终对准的只是云南省高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仅在事件曝光之初表态正在审查此案,此后人们也只有在《再审决定书》中才看到云南省检察院出具《检查意见书》建议重审此案,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始终没提起抗诉,两者均因此得以撇开这趟“浑水”。[4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云南省检察院的做法事实上把云南省高院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在一定程度上,部分人对再审理由、程序的质疑与此有关。[42]
由此看来,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其实处于复杂的关系-权力结构之中。“法律的社会实践事实上就是‘场域’运行的产物,这个场域的特定逻辑是由两个要素决定,一方是特定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是司法运作的内在逻辑,前者是为场域提供了结构并安排场域内发生的竞争性都只(更准确的说,是关于资格能力的冲突),后者一直制约着可能行动的范围并由此限制了特定司法解决办法的领域。”[43]我们可以把法院审理案件这一司法场域理解为以法官为核心的由法官、当事人、代理人、其他案件参与人等构成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丛,这个关系丛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结构性的约束,这些角色、行动者的特性就取决于他们各自在这个关系丛中的位置以及由此决定着他们所能动员的资源、要达到的目标和个人禀赋。[44]在李昌奎案件演变的过程中,这一事件所处的场域比一般案件更为复杂,它在多重“场域”中实践。因为这个场域的关系丛超出了案件本身所直接涉及到的人员,包括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云南省检察院等不直接出现在舆论中却非常重要的部门。由此来看,云南省高院一系列看似相互矛盾的辩护、选择以及最后的孤立境地也就成为了可以被理解的——这当然说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
(四)骑虎难下:非典型“难办案件”
至此,可以较清楚地看到李昌奎案件是如何、为何如此演变的。那么,这样一起案件为何是难办案件呢
苏力教授提出:
“有别于案情复杂、事实不清的‘疑难案件’或影响巨大的‘重大案件’,难办案件(hardcase)事实清楚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适用,或适用的结果不合情理甚或有悖‘天理’(所谓自然法),法官因此面临艰难抉择,需要‘造法’或通过解释‘造法’,但这不仅有悖执法者的角色,受制度制约而且可能引出坏法律。许霆案就是一个难办案件。”[45]
笔者认为李昌奎案则属于另一种类型的难办案件,无论法官如何决策,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都不能取得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其最大的特点其实也为云南省高院有关负责人所感受——“骑虎难下”。具体到李昌奎案件中,云南省高院把昭通市中院对李昌奎的死刑判决改为死缓,这一案件成为了社会舆论焦点,至此,此案从最初的简单案件演变为难办案件。因为,如果不启动再审程序会进一步激怒民众,展示的是司法的傲慢和独裁,[46]引发民众对司法丧失信心;启动再审,如果不改变二审判决,必定被民众批评为法院“走形式”或被批评为轻易启动了不必要的再审;启动再审,如果改变二审、回到一审判决,满足了民众的基本公正感,却有舆论左右司法之嫌甚至被一些人批评为司法缺乏稳定性和独立性(或许,这种伤害感主要是司法机关内部的感受)。总之,无论最终如何判决,司法的权威和民众对司法的信心都会在不同程度或不同方面受到损害,司法机关已经没有了最优的选择,所能做的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李昌奎案的演变还表明,这种类型的难办案件其实是司法机构一手造成的,其根源于司法系统内部。在这一实践的进程和关系格局中,不难发现,司法系统内部并没有就如何去维护法律权威达成共识——这正是司法机构法律世界观紊乱的直接表现,这种紊乱的世界观在于无法准确定位法律在社会生活与文化脉络中的位置和意义,也没有健全的司法理念,它无法弥合民众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分歧——而这种弥合正是司法者的职责之一。
三、并非中国特色:民众舆论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李昌奎案戏剧化的发展过程被有些人归结为司法不够独立、司法缺乏公信力等问题。的确,在这一过程中媒体、舆论起了重要作用,以司法机关最初的漠然来看,没有舆论井喷断然不会有最终的再审。但是,在民众舆论影响司法以及法律观的交战问题上,并非中国特色;人们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低信任度也并非中国特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合理、不恰当的司法就该被容忍。
(一)司法公信力:单维还是多维
在整个事件的辩论过程中司法公信力始终是云南省高院部分法官和部分媒体用以和民众辩论的重要理论、话语资源,以至于评论把李昌奎的争议焦点归纳为“杀人偿命VS少杀慎杀;程序正义VS结果正义;独立司法VS民意不可违”。[47]云南省高院一位匿名法官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说道:
“在轰轰烈烈的‘民意’反映上,法院应该坚持正确的底线,司法屈从于民意、无原则的跟风,是扭曲的司法,是无权威的司法。
但愿在李昌奎案这场‘博弈’中,不让舆论的压力影响到司法的独立与公正。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法律的胜利,法治的胜利。”[48]
在云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前夕,著名刑法学家贾宇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李昌奎案如果因民意压力而改判将伤害司法公信力。[49]云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后,云南省高院一位参与李昌奎案的法官告表示,李昌奎案只要是判死刑,不管是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缓,法律适用都是正确的。判死缓并不算错。这位法官说:“我们希望任何人都不要借助外力来干预我们的司法,特别是终审判决的结果。这并不是法治的体现,相反这样看似公正体现民意的再审,却是对法治社会最大的伤害。”[50]
姑且不管以上论调中无视了中国法律尚存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死刑制度,单就这些言论中对于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的理解来看已是残缺不全的。
按照以上论断,司法权威、公信力仅仅是来源于司法独立,其背后实则把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关系中,或者认为只要有程序公正就能保证公信力。然而,“司法信任并不是一个一维的概念。”[51]人们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信任来自于多维的要求,包括程序公正,还包括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性、有效性,不仅要求程序正义也包括实质正义。在程序与实体之间并非对立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手段和目的关系,二者在根本上有着各自独立的价值。对于公众能否获得一种公正感,二者缺一不可,是撑起司法权威的两条腿。在中国刑法的实践中,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这本身就是法律系统中巨大的不完善,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前提下说“李昌奎案只要是判死刑,不管是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缓,法律适用都是正确的”实在是无视了二者在法律实践中的重大差别,表现出对死刑、刑罚的社会意义和功能的完全无知(或许是故意无知),更是污蔑了民众的常识和感知公正的最基本能力。这样一个在实体上已经明显错误的案件,如何可能通过所谓的司法独立来保持司法的公信力 即使在著名的辛普森案件中,即使有巨额的民事赔偿,但是仍然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损害了公众对此案中“获得胜利的美国司法制度”的信任。[52]在所谓的现代法治国家中,对于错误的刑事案件的重审、复查也是必须的。[53]
(二)量刑改革的努力:弥合公众与司法系统之间的分歧
那位不愿署名的法官还说到:
“在中国的法制语境中,法等于罚,法就是长着牙齿随时吃人的东西。在封建社会,除了笞、杖、徒、流、死,中国人还发明了各种折腾人的刑罚。几千年来,中国法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忆慢慢变成了一种‘惩罚’的常识和暴力传统,即‘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由此可见,死刑改死缓的争议,实质是触动了国人传统观念中‘杀人必须偿命’的死刑观念。
我们必须保持刑罚应有的人道和谦抑,消除对杀人的迷信和崇拜,不能再把杀人当作是治理犯罪的灵丹妙药。
我们不仅要为民族振兴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顺应世界潮流,更重要的是转变我们的刑罚理念。”[54]
如果脱离该文的语境,单看该文行文无疑属修辞意义上的美文;如果不是在李昌奎这样一个案件中,这些文字也必定能够打动不少人。但是,在李昌奎案这一具体的争议中没有非黑即白的界限,首先,死刑并不等于酷刑,并且正如伦理学教授肖雪慧所说“支持死刑不等于选择野蛮”;[55]第二,中国并没有出现过杀人崇拜,这是对古人的妖魔化,今天的民众也没有这样的情形;第三,什么是“顺应世界潮流”、是谁的潮流在一个有争议的具体案件中将无的放矢。
民众对李昌奎改判死缓并没有狂欢的意味,而是愤慨。正如桑德尔所言:“愤慨不止是一种欠考虑的怒气,它表明了一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道德论证。愤慨是当你认为人们得到他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时,而感到的一种特殊愤怒。这种愤怒是对不公正的愤怒。”[56]在刑事司法的领域,罪刑相当是公众最基本的公正需求。众多研究表明,“公众的看法与司法体系之实践之间巨大的差异的存在会破坏刑事司法制度的合法性基础。”[57]也正因此,众多的国家不断寻求弥合公众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的错位,尤其是在量刑领域。
李昌奎事件引发的舆论交战中,那些无视二审存在着严重错误而祭出司法公信力和废除死刑这两杆大旗的人们,对于司法权威、法律效力乃至法律系统合法性来源的认识完全是单维甚至偏执的。如果我们赞同巴拉克的说法:“弥合法律与社会的差距是法官的核心任务”,[58]那么在李昌奎案件中,并没有看到法官就弥合二者之间的差距进行过积极和有效的努力。或许问题不仅出在法官身上,更重要的是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的巨大差异包括罪犯命运的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民众社会心理的巨大差异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李昌奎案件中云南省高院的改判导致量刑制度和刑罚的类别的不完善凸现出来,致使人们难以接受对李昌奎之类的罪犯的宽大。这也是笔者失望的地方,云南省高院的二审决策事实上非但没有弥合法律尤其是不完善的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差距,相反,还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差距;非但没有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相反,是对二者的削弱。
(三)究竟谁能影响司法:被忽略的政治
整个李昌奎事件中,云南省法院部分法官和学者对民意及再审的反击主要集中在前述民意干扰司法之类的问题上。但是,我们应该认真地问问:究竟谁/什么能左右司法
似乎在被标榜为法治国家的司法中,民意并不能影响司法尤其是个案的审查,这被某些人奉为圭皋——但这只是神话。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史甚至出现过因一部电影而引发改判的案件。1988年,美国人埃罗尔·莫里斯拍摄了一部电影所谓的“纪录片”《细细的蓝线》(The Thin Blue Line),在片子中曝光了一个被错误指控谋杀警察并被判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的案件,由于这部电影引起了轰动性的舆论,法院立即展开对该案的复审,最终使当事人沉冤得雪。
民众舆论当然会影响司法,但是通常来讲,民众不会直接影响司法,而是民意影响着政治,政治再影响了司法,司法从来都是政治的一部分。一些研究中明确地指出:“立法和行政机关一般不能通过法律规章推翻法院根据宪法作出的判决,但是他们能够采取措施惩罚‘犯错误的’法院,不仅使得法官们无法实现其政策目标,而且这些措施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正当性。”[59]另一些研究则表明在选举制之下,“的确有大量的证据显示法官们不会忽视民意。学者们的研究发现,高票当选的法官更倾向于压制不同的意见,并会在裁决中反映民意。”[60]和许多国家一样,[61]中国法官不是经由选举产生,当然不需要对选民负责。但是,司法作为国家统治的一部分,[62]统领司法和行政的政治机构必须关注司法,防止因司法偏离民众的基本正义感而引发社会对整个政治系统的不满。这对于理解李昌奎事件中云南省法院的态度为什么发生急剧转折甚为重要。李昌奎案件的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是,如果说微博、博客、论坛以及报纸是民意的呈现方式,那么,并不是所有的民意都能够引发司法机关的重视。即在民意呈现的表像之下,还必须有机制和途径来真正触动司法系统做出反应。而这正是理解民意是否真的能“绑架”司法的关键。虽然我们似乎始终没有机会从已有的报道、信息中知道究竟是什么、是谁直接促成云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 但是,显然并不全然是所谓的民意。如果网络能够直接引发再审,那么,许多案件,比如同样由云南省高院改判死缓、引发舆论关注的赛锐杀吴倩案现在也不至于杳无音讯。甚至可以说,云南省高院再审李昌奎案件与赛锐案的石沉大海,在原理上、逻辑上是相同的,相互矛盾的表象背后往往有其一致的逻辑。简单地断言李昌奎案再审是民意“绑架”司法,既有失于对公正司法的理解,又有失于简单化地看待民意、司法和政治的复杂互动和关系。
而在另一些研究法官职业的作品中表明:法官之所以遵循先例,是因为“法官的等级制:因为下级法官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判决被‘上级’推翻,所以他们会遵从上级法院建立的先例……最高法院进行复审的威胁,可能会诱导中级上诉法院的法官遵循其上级法院的命令。”[63]从这个角度讲,云南省高院以及所谓“赛家鑫翻案风”中的其他法院为什么在没有枉法的情况下,要把那些罪行极其严重、对国家安全无妨的罪犯改判死缓就能够被理解了。这其中的原因正是地方法院所无法明言却又必须心领神会的。
种种情形表明,法官、法院事实上处于政治、民意、法律交织而成的场域,法官的选择是综合了规则、约束、资源和目标的结果。问题在于,在一个世界观紊乱的场域里,司法、法官很容易走向歧路——忘却了司法为谁负责。
四、讨论:建构法律沟通的理性之路
(一)司法引领社会变革:先找到钥匙
在李昌奎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最强烈的废除死刑的呼声。之所以说最强烈,并不是主张者众,而是连贺卫方教授等这些明确表示主张废除死刑的学者面对李昌奎案件也有些犹豫和保守了,[64]在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情况下,还是有人坚定地说:“死刑是时候改变了”。[65]
某些人以一种精英式的话语指责中国民众残忍、好杀,完全无视了人们也在众多的案件中反对判处死刑,在一些案件中甚至是同情心的泛滥;[66]也无视了刑法修订中减少死刑罪名并没有引发过严重的抗议。
人们热衷于“围观”死刑案件、发表热烈的议论,反映出的正是死刑所具有的复杂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67]与此有关的是,在人们並不完全信任司法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明知死刑可能带来冤假错案的情况下仍然支持死刑制度,这是为什么 这并不是因为民众是在“围观”、事不关己。相反,是因为人们对司法完全不受社会、民众的控制的担心超过了对司法的不信任感。直白地说,不完全信任司法是因为司法会出错,但是,如果司法完全不受控制那就彻底脱轨了。人们面对残忍的凶案时,如果嫌犯不被判处死刑,那么,民众对控制司法的无力感就会严重凸显出来。尤其是没有合适的功能替代制度的情况下,还会使人们感到社会没有能力和决心抵抗严重侵犯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行为和人。因此,李昌奎案中民众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甚至药家鑫案中民众的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神共愤、偏颇的舆论、不顾药家鑫悔罪表现的受害人亲属和判决,都是在某些“用心良苦”、“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死刑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位研究台湾刑法学者的告诫或许是一剂良药:
“反对死刑的菁英与人权斗士若不能真正理解死刑所代表的象征意义,正视死刑制度存在与仪式的发动在社会心理上的价值,以此进一步去思考如何将每一个犯罪者‘带回人间’,或是在制度上积极地回应、或取代死刑所具备的象征意义与社会功能。那么,反对死刑的菁英跟支持死刑的大众(以及司法菁英)间,或许永远会存在各说各话的局面。”[68]
打着废除死刑的旗号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令人遗憾,而如果真的是认为司法可以引领社会变革,那就是轻率了。或许我们回顾一下苏力教授那“保守”的主张是有益的:“一个社会的法律的合法性最终必须而且只能基于这个社会的认可,而不是任何外国的做法或抽象的原则。”[69]
我想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废除死刑,而是司法如何才能引领变革。这一问题反映了我们对法律、司法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在法学领域从来都有不同的主张,主张法律可以改变、塑造社会者视法律为裁剪和形塑社会、实现理想的剪刀,主张法律受制于社会者视法律为反映社会的镜子。[70]其实法律既不会完全由社会摆布,却也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的基本情况实现和引领社会的变革,尤其是面对那些长久以来的风俗、观念,法律变革社会的理想常常遭遇严重的抵抗而失败,典型如美国的禁酒令。[71]立法、执法领域尚且如此,司法的影响力就更小了。司法变革社会的想法往往是法律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神话之一。著名如1954年的布朗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这一案件被视为司法扭转种族隔离的典范。然而,据罗森伯格的研究,此案对南方公立学校的整合贡献很小,真正起作用的是其他政治部门和广泛兴起的民权运动。[72]
司法改变社会只能是在特殊的环境、情形下发生,而这取决于司法变革能否满足维持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社会功能和心理需求。如果说司法或许能够加速社会变革,也只能在具备基本的社会条件下因势利导。李昌奎案彰显的是在死刑的社会功能没有替代性制度的情况下遭遇的司法能动失败,禁酒令是在完全忽视了酒的社会功能的情况的道德法律化失败,而布朗案之所成为后来追加的典范则是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李昌奎案是司法引领废死运动的象征性实践,它像我们要经由一道关闭的大铁门进入桃花源,在没有寻找钥匙情况下,我们直接拿起铁锤试图破门而入。这是对司法与社会的关系的误解,是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间的失衡。让我们一起领悟一下智者的教导吧:
“这是否意味着只要存在这种差距(法律与社会——笔者注)法官就应当弥合之 如果是这样,我就会支持运用绝对的司法能动主义以实现这一职责。但是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我支持渐进的法律变革……我讨论了通过稳定性实现变革的需要;我强调了根据制度的一般框架、规范一致性、有机体的生长、自然发展、连续性与一致性的进行变革的重要性。我注意到,当法官弥合法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差距时,他必须考虑制度的约束,包括改革的偶发性、他可能获得的不完全的信息以及缺乏足够的法律工具……
这些因素得出的结论是:法官通过部分能动、部分克制可以最好地弥合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完全的能动主义或完全的克制不仅不可能,也不可取。”[73]
(二)在事件流中交战并辨识法律的社会意义
人们对法律、法律实践往往缺乏直接的了解,尤其是对法院、法官,大部分人一辈子也不会跨进法院一步。那么大众如何形成对法律、司法的认识
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裁剪着事件,讲着各种故事,对于人们认识这个世界包括法律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人们提供了关于法律的间接经验,使人们以为自己了解现实。各类媒体和各种交流工具的兴起使民众得以讨论、监督司法,使人们有机会不必亲自参与司法实践就能够了解司法及其问题。
然而,当民众与各种不同形式、性质的媒介发生联系时,民意就会发酵。微博、QQ、各种论坛使人们的各种行动得以摆脱时空对交往的限制,世界也因此加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在参与着各种案件的讨论,破除了对法律系统的信任。在李昌奎案中人们怀疑这是为了另一起免死案件做铺成、许霆案中人们怀疑法院的量刑是否真的能做到公平、泸州“二奶”案中人们怀疑法律能否保卫道德、“躲猫猫”事件中人们严重怀疑公安能否保护被收押者、赛锐案中人们的各种怀疑还在继续……网络时代的到来,使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广泛参与、监督法律的民众能够透过网络把对法律的担忧、怀疑以一种极为强大的方式表达出来。可以说,在媒体无所不在的世界,法律实践不再完全是秘密,而人们首先发现法律不像想象的那样可靠,法律总是会出错。媒体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法律系统信任的危机。
我们还会发现,对于非当事人来讲,媒体所提供出来的世界、事件和当事人所面对的并不相同。简单地说,媒体喜好轰动的情节却厌恶复杂的事实,它像剪刀,裁剪着当事人所共同面对的世界,把它简化为后来读者、听众所看到和听到的样子。因此,媒体必定会有偏颇,在不同的事件中无非是偏颇程度不同。[74]李昌奎案件中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非常严重的歪曲,但是从犯罪学的角度仍然会发现李昌奎有其值得同情的一面,他的凶残也是可以被理解的,而这些在舆论中被忽略了;药家鑫案中的张显正是动用了媒体煽情、扭曲的一面形成了失真的“事实”,媒体的确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在担忧媒体对司法、法治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同样有理由相信,传媒提供出不同以往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去反思法律、法治。
因为,传媒与司法的个案是事件流,而非单个的案件。例如,在药家鑫被判处死刑之后,不仅有药家鑫父亲状告张显——这使我们认识到之前有许多情绪来得实在没理由,甚至张妙父亲也在反思:“药家比我更惨,我还有两个孩子,而药家什么都没有了……”[75]而最近张妙亲属又向药家索赠,无疑让人们必须继续反思下去;人们之所以关注李昌奎案件,不仅仅是李昌奎实施了残忍的奸杀,还因为“药家鑫案”成为了该案的“前传”,而“赛锐案”则是“后传”。人们关心的其实是一批批案件。在这样的事件流关注中,我相信许多人正在形成关于什么是公正的司法的看法,也正在反思着自己对某一案件所持有的情绪或观点。
最为重要的是,媒体的发达使人们关于法律的辩论成为了可能,使不同的法律表达、法律观得以展现和交锋。
在李昌奎案件中,法院、法官、民众、专家持有的不同的观点得以呈现,展示了一个多元并且相互抵牾的法律观途径,这或许多少会令人沮丧。然而,这正是媒体的价值所在,它提供出反思的机会,人们得以认识到不同于己的立场——这些本来就存在着,媒体所做的是让人们感知到。这种多向度的沟通中,使法律的社会意义最终能够被辨识——这一点对于立法、司法机构和政治家尤其重要。
所谓的法律精英必须意识到,人们无需专门学习法律也能够对杀人、婚姻问题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提出法律意见,因为这种表达依赖于常识、常情、常理,也因为这些问题关系着人们对社会能否获得正义、能否对抗恶行之类的深层心理反应。那些以法律的专业化作为盾牌的法律专家其实是无视人们能够感知公正和正义的能力,并忽视了法律实践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法律所具有的特性及其所受的来自于社会的约束。如果司法想达到某种政策、改革目标,首先要让民众接受它的重要性并满足人们最基本的心理需求,而不是让人们遭受到极端司法能动的一意孤行。
另一方面,李昌奎案从一个简单案件演变成为一个事件、难办案件,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律世界观的紊乱并非完全来自于民众对法律的“无知”、对所谓法治精神的“蒙昧”。相反,从民众与法院、法官的交战中,以及司法机构对于这样一起简单案件的处理、面对公众的方式、曲折反复的态度足以表明,在法律精英聚集的地方、在司法机构内部其实埋藏着外人不易察觉的紊乱的法律世界观,而这种紊乱或许才是阻碍着法治前行的暗桩——这对于人们认识法律的社会意义也尤为重要。
或许,对我们来讲,重要的不是对个案的执着。而能否保证民间与官方的不同法律表达得以畅通,以此促进不同的法律观之间的交流,改善法律的构造,实现法律意义的融贯;在辨识法律的社会意义过程中弥合过度分歧的法律观和公正观,调适紊乱的法律世界观。这其中,尤以司法机构及其人员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社会面前、以一种什么样的话语方式展开对话最为重要。李昌奎案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是,司法系统本身也是一个政治的场域,法官在这一个场域中所受的规训使其往往忽略了他真正应该的对话对象是谁并在关于司法究竟为谁负责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最终伤害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
司法机关可以选择向民众扔去击碎其心灵的一颗颗炸弹,也可以像春雨一样润物于无声;可以选择“专业化”、“潮流”、“文明”作为盾牌把民众的朴素正义观拒之于千里,也可以选择对话、交流和迂回、渐进的改革。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可以在现实的约束与无限的可能性之间作出选择——这恰是希望所在;而选择什么,则取决于你的立场——法律世界观。
【主要参考文献】
1.[美]奥斯汀·萨拉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高鸿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美]克里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载《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4.[以]巴拉克:《民主国家的法官》,毕洪梅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5.[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6.[英]朱利安·罗伯茨、麦克·豪夫:《解读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态度》,李明琪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宾凯:《从决策的观点看司法裁判活动》,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
8.陈柏峰:《传媒监督权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载《法学家》2012年第1期。
9.方乐:《中国法需要什么样的世界观 》,载《法学家》2011年第3期。
10.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雷磊:《融贯性与法律体系的建构》,载《法学家》2012年第2期。
12.李佳玟:《死刑在台湾社会的象征意涵与社会功能》,《月旦法学杂志》2004年第10期。
13.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
14.王启梁:《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
Judicature,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s at An Age of Disordered Legal World View: A Study Centered on the Case of LI Changkui
WANG Qiliang
The Case of LI Changkui represents a kind of simple “hard case”, in which whatever the judge made a decision, result of the case failed to gain good social and legal effects, and the causation, however, rested on the internal system of judicature. The Case of LI reflects an age at which legal world view is deficient in cohenrence and integration. Although it’s not an exclusive problem for China that judicature,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s interact complicatedly, and the society shows distruct upon the crinimal justice system, it reveals that, in the case of LI, some judicial personnel and academics hold an unidimensional and prejudiced understanding on the credibility, legitimacy and stability of judicature. It’s argued, based on the case of LI, that judicature should operate to bridge, rather than widen, the gap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hanging society, judicature has to meet the public’s basic psychological demands upon equity. It’s also argu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has contributed to help the public identify and understand the social meanings of the law in a flow of events. In this sense, it becomes possible to achieve some coherence among plural legal wotls views.
Keywords Legal World View; Coherence; Hard Case; Social Meaning of the Law; Death Penalty
Wang Qiliang, Ph.D in Law, Professor of Yunn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本文的写作得到李娜女士、李佳玟教授、宾凯博士的重要的帮助,特此致谢。
[1] 众多有影响力的媒体均设置专题报道、讨论该案,如凤凰网:《聚焦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载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lichangkui/ ,2011年9月20日访问;雅虎:《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载雅虎网http://news.cn.yahoo.com/yunnanlichangkui/ ,2011年9月20日访问;腾讯网:《云南“赛家鑫”改死缓的疑问》,载腾讯网http://view.news.qq.com/zt2011/lichangkui/index.htm ,2011年9月20日访问。
[2] 关于这两个案例的研究甚多,对许霆案较为集中的讨论可参见《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第4期以及2009年第1期刊载的陈瑞华教授等撰写的若干篇论文。有关梁丽案的讨论参见桑本谦:《传统刑法学理论的尴尬(Ⅱ)——面对梁丽案》,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3] 参见陈卫东:《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曲新久:《当刑讯逼供遭遇黑社会——刘涌案的启示》,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4] Sally Falk Moore:《法律与人类学》,黄维宪译,载李亦园编:《文化人类学选读》,(台湾)食货出版社1980年版,第200-208页;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强世功等则是中国法学界较早运用这一方法的学者,见强世功:《“法律”是如何实践的》,赵晓力:《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6] 王启梁:《乡土社会的变迁与法治的困境》,载苏力主编:《法律书评》第十辑,即将出版。
[7] 王启梁:《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131-154页。
[8] [美]克里福德·格尔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载《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9] [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一世纪的历程》,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0] [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353页。
[11] 方乐:《中国法需要什么样的世界观 》,载《法学家》2011年第3期。方乐在文中还指出:“在因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自身地位的变化以及全球法律秩序重构的多重背景下,中国法的发展无疑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应当强调中国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多维、立体的世界,要求中国必须在开放的结构中对这个丰富的世界予以多元化的理解, 以便主动作出恰当且灵活的因应之策; 而且重要的是,这一世界观也应当将中国从世界经验与中国体验的‘客体’走向‘主体’,还要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
[12] [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36-166页。
[13] 雷磊提出:“所谓法律的融贯性,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推理的融贯性问题,二是法律体系的融贯性问题。”见雷磊:《融贯性与法律体系的建构》,载《法学家》2012年第2期。整体论和对融贯性的追寻对于法律的实践以及法律文本内部的协调和融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使法律体系内部的结构和逻辑周原变得可能,也使得法学作为一门研究规范的学科具有一种“科学性”。但是,这种整体论的局限也相当明显,因为它仍然主要是在法律文本之间和法律体系内部来展开的。笔者所说的“融贯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与雷磊文章所指的法律体系的融贯性相似,也与科尔曼所提出的“原则的实践”、德沃金的“整体论”有关,主要是司法审判、法律适用、法律体系建构中的融贯;第二方面,融贯性是把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放在社会整体中来看待,指向的是法律与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的关系,接近人类学中的整体论,强调的是法律与外部环境(社会、政治、多元的法律观等)的沟通、兼容和融贯的问题。详细探讨参见王启梁:《通过人类学研究法律如何可能》以及《人类学视角下的法律融贯性》,未刊稿。
[14] 宾凯:《从决策的观点看司法裁判活动》,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
[15] “政治”是一个具有多种面向、难以定义的概念,有关学说见Barrie Axford等:《政治学的基础》,徐子婷、何景荣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4页。
或许采取一种宽泛而又语境化的理解方式较为适宜。因此,本文所涉及的不同问题中主要有如下几种从宏观到微观的情形:国家间的政治,如死刑的国际人权压力;中央与各级政法机构的关系;不同层级司法机构间的关系;司法系统内部的组织和决策;司法机关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民众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某个事件中的决策;关键性人物的行动或表态。
[16] 王峰:《李昌奎“命案”漩涡》,载《法制与新闻》2011年第8期,或见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8-11/140322974257.shtml,2011年8月12日访问。
[17] 微博名“王家飞的哥哥”,地址:http://t.qq.com/w365430529/ 。
[18] 格祺伟、张桓瑞:《男子奸杀两人获死缓激发民愤 检方已受理家属申诉》,载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txt/2011-07/05/content_22923988.htm,2011年7月5日访问;佚名:《云南省高院重新审查李昌奎案 两天内将公布结论》,载《生活新报》2011年7月6日。
[19] 同注7,第120页。
[20] 徐讯:《中国司法与媒体关系现状评析》,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21] 曹红蕾:《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续 省高院:派专人重审此案》,载云南网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1-07/05/content_1700317_3.htm, 2011年7月5日访问。
[22] 同注21。
[23] 曹红蕾:《省高院回应奸杀少女摔死男童案:判决程序合法未徇私舞弊》,载云南网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1-07/07/content_1705418_3.htm, 2011年7月7日访问。
[24] 佚名:《云南省高院重新审查李昌奎案 两天内将公布结论》,载《生活新报》2011年7月6日;王琳:《李昌奎案二审究竟错在哪 》,载腾讯网http://view.news.qq.com/a/20110720/000041.htm,2011年7月20日访问。
[25] 刘子瑜、都力维:《我骑虎难下,但死刑是时候改变了》,载《新快报》2011年7月13日,或见该报网页http://epaper.xkb.com.cn/view.php id=708807,2011年7月15日访问。
[26] 李佳玟:《死刑在台湾社会的象征意涵与社会功能》,《月旦法学杂志》2004年第10期。
[27] Kennedy指出:死刑与其他刑罚之不同处在于,期制度的存在与仪式的运用,最能够彰显这个社会的决心,显示这个社会能否并愿意提供一个终极的手段,来处理对这个社会之秩序与道德最严重的犯罪。同注26。
[28] 例如中央电视台2011年7月13日播出的节目《新闻1+1 李昌奎案:情与法 罪与罚》中云南省高院的法官为二审改判进行辩护,而主持人或许是出于维护法院权威的考虑,在最后的总结中具有较明显的为云南省高院辩护的倾向,见中央电视台网站http://news.cntv.cn/society/20110713/109021.shtml,2011年7月20日访问。此节目播出后引来民众激烈的批评。而节目中作为专家嘉宾的北京大学的车浩博士以极为专业和中立的方式解释了云南省高院二审的逻辑,本意是不主动伤害司法的权威,虽然其明确表示不认同云南高院的民众“狂欢论”并用委婉、曲折的方式表示并不认同云南高院的二审判决,还是遭到网友炮轰。
[29] 关于省高院为二审所做释法辩护的不当之处在事件发生期间已经立刻出现了众多的批评,而后也有不少批评性学术论文,笔者对此不再赘述。见车浩:《从李昌奎案看“邻里纠纷”与“手段残忍”的涵义》,载《法学》2011年第8期;姜涛:《从李昌奎案检讨数罪并罚时死缓的适用》,载《法学》2011年第8期;桑本谦:《“标杆” 还是“警示牌” ——解读云南省高院改判李昌奎案引发的舆论风暴》,未刊稿。
[30] 格祺伟、张桓瑞:《云南高院决定另组合议庭再审李昌奎杀人获死缓案》,载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ociety/1/detail_2011_07/16/7738104_0.shtml,2011年7月20日访问。
[31] 武威:《“赛家鑫”翻案成风 》,载《广州日报》2011年8月4日。
[32] 王琳:《死刑的距离有多远 从中院到高院》,载雅虎网http://opinion.cn.yahoo.com/ypen/20110723/485819.html,2011年12月26日访问。
[33] 赵蕾:《关注死刑:云南高院的中国式处境》 ,载南方周末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61895,2011年8月4日访问。
[34]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35] 虽然“指标”性质不同,但是一篇讨论基层公安指标考核与执法的文章对于理解这类问题仍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见易江波:《被数字型塑的生活:指标督责型治理下的基层生存状况——以派出所办理吸毒案件的参与观察为基础》,载《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第5期。
[36] 据一篇调查性报道,可以看出死刑复核程序对下级法院确有约束性和诱导性,见刘长:《少杀甚杀 进退维谷》,载《新世纪》2011年第35期(或见财新网http://magazine.caixin.com/2011-09-02/100297710.html,2012年1月5日访问)
[37] 司马当:《李昌奎案错在哪里》,载东方法眼网http://www.dffy.com/fayanguancha/sd/201109/24999.html, 2011年11月2日访问。
[38] 王绍涛:《从药家鑫到“赛家鑫”,死刑的标杆在哪里 》,载王绍涛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7668330100s41i.html,2012年3月3日访问。
[39]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40] 陈兴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考察:以刘涌案和佘祥林案为标本》,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41] 笔者个人猜测,之所以没有提起抗诉,可能是省检察院过度地考虑了检法两家的关系,避免提抗导致法院难堪。但是,这却在客观上对于树立司法权威不利,并且也导致了法院的孤立。
[42]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检察院对法院的判决发检察建议书是极其罕见的。发检察建议书在此案中并不够严肃,检察院的意见应当以抗诉来表达。他认可云南高院再审的合法性,认为法院自己发现错误自己提起再审,符合现行法规定,但同时带来一些程序上的疑问:比如,重新组成的合议庭,仍是先前作出死缓判决的云南高院审判委员会下属的审判组织,此案最终仍将提交到同样组成人员的审委会去讨论,这就带来回避上的问题。“同样的一批人,在几个月后,他们的死刑观念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游伟认为,最好的形式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然后指定其他省的高级法院再审。见陈霄:《云南高院启动李昌奎案再审程序被指丧失法律权威》,载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lichangkui/content-3/detail_2011_08/10/8296045_0.shtml _from_ralated,2011年8月11日访问。
[43] [法]皮埃尔·布迪厄:《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强世功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99页。
[44] 王启梁、张熙娴:《法官如何调解 》,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5期。
[45] 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
[46] 王琳等:《法学家谈李昌奎案:法院有错不改是司法独裁》,载腾讯网http://news.qq.com/a/20110824/000323.htm,2011年12月26日访问。
[47] 武威:《“赛家鑫”翻案成风 》,载《广州日报》2011年8月4日。
[48] 佚名:《死刑不是灵丹妙药,民意不能替代法官审判》,载《南方周末》2011年7月14日,或见南方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61306,2011年7月14日访问。
[49] 《华商报》专访:《法学专家谈李昌奎案:因民意压力改判伤害公信力》,载台海网http://www.taihainet.com/news/cnnews/2011-08-20/737291_2.html,2011年8月20日访问。
[50] 佚名:《李昌奎案办案法官:再审看似公正实则伤害法治》,载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lichangkui/content-3/detail_2011_08/03/8138060_0.shtml,2011年8月3日访问。
[51] [英]朱利安·罗伯茨、麦克·豪夫:《解读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态度》,李明琪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52] 同注50,第40页。
[53] 一篇模棱两可的评论中提出:“美国司法制度也是尊重终审判决的,199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判例里主张:宪法并不保障各州已经定罪的在押犯不被执行死刑,即使有新的无罪证据,因为这种翻案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是必然的。”沈彬:《李昌奎案再审,死刑离正义还有多远》,载腾讯网http://view.news.qq.com/a/20110823/000004.htm,2011年8月24日访问。笔者不知沈彬先生所据何来,也不明白其要表达和追求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法律也无非是恶法,这样的判例也必定会被抛弃。难道就因为它是“美国制造”我们就必须俯首学习吗
[54] 佚名:《李昌奎案办案法官:再审看似公正实则伤害法治》,载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lichangkui/content-3/detail_2011_08/03/8138060_0.shtml,2011年8月3日访问。
[55] 肖雪慧:《支持死刑不等于选择野蛮》,载南都周刊网,2011年7月12日访问。
[56] [美]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朱慧玲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57] 同注51,第2页。
[58] [以]巴拉克:《民主国家的法官》,毕洪梅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
[59] [美]奥斯汀·萨拉特主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高鸿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60] 同注59,第187页。
[61] [美]史蒂文·瓦戈:《法律与社会》,梁坤、邢朝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6页。
[62] 王启梁:《当代中国正式社会控制的图景与困境》,载张永和主编:《社会中的法理》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63] 同注59,第195页。
[64] 贺卫方:《司法如何纠错》,载贺卫方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2drlq.html,2011年8月29日访问。
[65] 同注25。
[66] 如王斌余案,参见桑本谦:《理论法学的迷雾——以轰动案例为素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3-100页。
[67] 同注26。
[68] 同注26。
[69] 苏力:《道路通向城市》,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70] 同注7,第264-272页。
[71] [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译,第63-65页;塞德曼夫妇也很强调法律引领变革的困难和误区,见[美]安·塞德曼、罗伯特·B·塞德曼:《法律秩序与社会改革》,时宜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2] 同注59,第198页。
[73] 同注58,第252、254页。
[74] 例如宜黄事件中的新闻报道,参见陈柏峰:《传媒监督权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载《法学家》2012年第1期。
[75] 见中央电视台节目《专访药家鑫案双方父母》,2011年8月14日,载中央电视台网站http://news.cntv.cn/china/20110815/100482.shtml,2011年12月28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