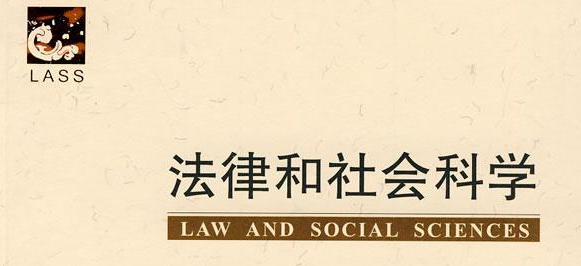受《法律和社会科学》的委托,由我担任其中一辑的执行主编。现在这辑的主题是“边疆的法律”,最初,它不叫这个名字。2013年11月9日,“法律和社会科学”年会结束当晚,我和侯猛、赵旭东等师友在昆明文林街一家著名的酒吧聊天,讨论这辑专号的主题,定名“法律的边疆”。

一
“法律的边疆”,是一个模糊得让人能够充分展开想象力并带有人类学意味的主题。我们最初为这期专号设想了两个大的面向。
第一个面向,承袭了以往我们对“边疆”一词的理解,主要是和国家的某些区域、边界和历史联系在一起。这包括诸如,关于边疆治理的实践、统治的策略、法治在区域的施行,特别是法律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起到何种效果的问题。而这一面向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讲,都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基本问题。
第二个面向,寓意法律/法律人止步于某些所谓“边缘性”、“非主流”的社会领域。但其中的问题可能正在挑战着法律的核心地带,挑战着社会既有但不必然合理的秩序。例如,艾滋病、同性婚姻、生物技术、家庭暴力、非正式秩序、非正规经济,等等。这些问题似乎远离生活主流,远离法学主流。然而,它们对生活的影响正在日益加剧和迫近,并穿越了法律学科的既有分类。如何面对、解释和处理这些问题,超越了传统的法学学科的疆界乃至科学之间的分野。
这两个面向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边缘挑战、改变甚至动摇着中心。
在审阅和编辑本辑文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稿件较明显地集中在第一个面向的研究上。但是,部分文章也和第二个面向有关。戴溪瀛的文章“禁毒与防艾:云南田村的个案研究”虽然只是对一个村落禁毒防艾问题的微观研究,但从中可以看出毒品、艾滋病是如何破坏着一个社会的。在更大的范围看,我们曾经以为毒品、艾滋病只是“非主流”人群的问题,然而,所谓“危险人群”的边界正在改变。毒品、艾滋病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更大范围的社会的安危。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建构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去“再造团结”,这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1]这不是抄袭几部西方法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毒品、艾滋病的问题挑战了社会的安全,也挑战着法律人的智识。
易军的文章“通过宗教的纠纷解决——来自西部的田野调查”考察了信教村落中宗教与纠纷解决的关系及影响。这提醒我们必须面对信仰差异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了法律如何去面对这种差异。如果法律不能妥善地解决如何面对一个由世俗生活和宗教社会共同组成的现实,那么国家就会遭遇各种挑战和困扰。
人类学者嘉日姆几和石吓沙的“民族问题的非‘民族’因素”所发现的问题之一是,政府频繁的区划调整、体制变迁以及各种处理方案都参与了黑树林水利纠纷的繁殖与扩散。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纷争及其扩大经常来自政府的对纠纷的误判或者法律、政策的变化。对于身处“中心”的法律和政策制定者,对于基层社会、中国的国情就有多少了解,有多少关于现实尤其是“边缘”的真知灼见决定了法律和政策将迎接何种挑战。
林叶的文章“卷入‘发展’的边疆民族传统与反抗”细腻地描述和研究了一个政府主导的发展项目如何进入山地民族村庄,又如何在人们的“反抗”中遭遇了失败。当代中国典型现象之一就是国家带着“发展”全面进入社会,边疆地区也不例外。然而,一种带有片面而强烈的经济指标驱动的发展主义本身有着严重的局限。在这种发展主义的世界观里,没有对人的因素的深入考虑,也没有对地方性生活的必要观照。因此,就常常出现林叶所研究的边疆山地民众虽然被“卷入”发展,却又在隐蔽地“反抗”中重建着生活,这符合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的特性,这种特性中既包含了被动地卷入又隐藏着强大的抵抗能力,这无疑应该成为国家主导发展中进行反思和重视的问题。
朱苏力的“藏区的一妻多夫制”一文,不仅表现了对现实世界存在的制度进行社会科学解释的一种努力,更在智识上启迪我们去思考许多被忽略了的问题。他的文章不仅表明非主流的一妻多夫有其合理的依据和原因,而且,换个角度,普遍存在的一夫一妻也未必就一定是必须的。更有甚者,一旦某些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婚姻也未必一定是必要的。这无疑启发我们只要调整一下观察世界的眼光,我们就能感到传统的婚姻家庭法及其理论基础可能将面临着某些新的冲击,法律的中心地带将可能被晃动。
我们最终还是根据本卷文章的组成情况,将这辑专号重新定名为“边疆的法律”。对于第二个面向“法律的边疆”,将作为下一辑的专号。遗憾的是,由于某种原因,戴溪瀛和易军的文章没能刊发,但是在写作这篇手记时我还是保留了对这两篇文章的介绍,以便通过这篇手记呈现本辑的主旨。
二
边疆对于一个大国具有的意义以及它给统治带来的挑战,始终是每一个政权必须面对的问题。常安的“国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与边疆整合(1928-1949)”回顾和总结了南京国民政府面对一个多民族国家和广大边疆区域所可能出现的民族分裂和国家分裂问题,采取了国族主义话语建构策略和一系列边疆治理措施。与此形成呼应的是张剑源的“治边西南: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文章回顾和研究了历代中央政权如何统治和治理西南边疆的历史。李鲁岳的“新疆为什么要成立生产建设兵团”,则研究了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疆所采取的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制度创新,即不仅在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还设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王恒的文章“边疆与英国宪制的生成”虽然是讨论英国问题,然而研究表明“边疆不仅对中心地区宪制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还往往成为宪制创新的策源地,甚至取代旧的中心成为新的中心地区”,这本身就极具启发性。
这四篇文章涉及到不同的政权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采取的治边策略以及制度的创建和选择。但是,都能够指向一些共同的问题:第一,边疆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的来源。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获得长久的统治,都必须不断依据历史和现实调整治边方略,一系列重要的国家制度的创新与发展往往就来自对边疆问题的回应;第二,治理边疆的实践及其效果既体现了执政者的政治智慧,更是国家能力的综合体现。成功的边疆治理既需要领导者不断依据其所面对的国家和边疆情势进行制度的承袭、变革和创新,更需要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重要领域的调控能力。因此,边疆问题反映出的往往是中央政权的能力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边疆治理体系尤其是运用法治构建边疆治理体系是当代中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边疆会成为问题的来源 苏力、戴溪瀛、易军、林叶、嘉日姆几和石吓沙的文章,以及孙少石的“这里没有普通话:藏区的双语司法实践”,虽然关注的重点和要回答的问题不同,但是都反映出边疆地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第一,边疆地区基层社会中的各个民族因其文化或传统组织形式,而孕育出具有显著民族文化、地域特点的非正式规范和社会控制机制。这些自生自发的规范既是秩序资源,又可能和国家法律有某些冲突或不一致。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律实践,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苏力研究的一夫多妻制,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非正式制度。而戴溪瀛的文章探讨的就是关于法治如何整合少数民族社会中的规范和秩序资源,这种研究是理论上的探索,同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事实上,在实践中,早已有许多地方政府或基层组织请地方宗教权威结合社会问题、国家法律阐释教义,辨析是非义利,参与社会问题的治理。易军的文章研究了民族社会中宗教解决纠纷的机制、作用,并强调这种以和平主义为基调的机制对维护民族内部关系和处理矛盾所起的作用。宗教是民族社会获得团结、成员形成认同的基础之一,宗教提供了民族内部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机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如何处理跨宗教、跨文化的纠纷则是更为紧迫的、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我对易军下一步研究提出的要求。
第二,文化的多样性是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法治统一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这种多样性与国家法治统一之间的张力在边疆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在边疆地区,人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具有显著的多层次性,由此也会带来政治和国家认同的多层次问题。这一点在常安、张剑源的文章中也有所表现。不管是“羁縻政策”、“土官土司制”,还是民国政府的国族话语建构或我们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核心都是要解决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认同问题。
第三,民族问题、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不仅和宏观的国家制度架构有关,还和微观的法律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微观的实践中,区域的秩序和纠纷问题呈现出微妙和复杂的情形。嘉日姆几和石吓沙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民族志,从一个纠纷的长时段考察,可以看到所谓民族问题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建构之中,一起纠纷可能最初和民族间的关系无关,却会演变成民族问题,也可能通过非民族的因素的改变而最终化解。所以“民族问题依然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处理民族问题的主体、方式、观念、方案、甚至是组织依然可以参与民族问题的生成;这些过程往往随机发生,因此,民族地区各种社会问题都有着转化为民族问题的可能性。”这就启发我们去思考究竟应该如何处理纠纷和防止纠纷的民族问题化,法律在其中如何运作、能起到何种作用,以及民族问题可能存在着多种解决方案,这无疑需要着力研究和探索。
林叶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讨论,但是通过其研究,仍然会启发我们去思考:国家以各种形式进入边疆地区,其进入的过程其实是基层民众认识国家并在互动中形成对国家的印象的过程。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讲,国家形象直接关系着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也因此,需要多一些反思,国家究竟应该如何进入社会,国家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边疆,尤其是如何发展、发展什么
易江波的文章“‘做工作’:基层政法的一个本土术语”,是这些文章中较为特殊的一篇。一是其写作充分运用了公安“工作简报”这种经常被学者认为是“边角废料”的资料,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法律史和人类学对资料的把握和运用方法。二是这篇文章清晰地呈现了内地基层公安处理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纠纷的过程和方式。我之所以认为这篇文章重要,是因为易江波的研究指出“在来到内地城市的少数民族纠纷的化解领域,办案者‘做工作’的过程,既是基层政法的展开过程,也是当代中国的民族观以‘层累’的方式在基层与底层社会空间形成的过程。”可以说,由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并不局限在边疆地区,各地的法律实践过程,形塑了民众“关于民族、法律与国家的认知”,法律实践关乎着社会中民族观、法律观和国家观的建构和形成。因此,改善涉及少数民族、民族间关系的基层法律实践过程,其实关乎社会团结和国家认同。
对于作者们的文章,我无法进行全面的评析和梳理,其中的美妙和不足有待大家去发现。
三
2008年3月14日发生在西藏的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发生7.5事件,虽然举世震惊,但是大部分中心地带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和自己有什么关联,这无非是发生在祖国边疆的一次暴乱而已。我甚至可以肯定,在此之前,没有多少人关心和试图了解这几十年里,边疆究竟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着什么。然而,2013年10月28日发生在北京的“金水桥事件”和2014年3月1日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3.01事件提醒着我们,所谓边疆的事离我们并不远。在此之后,我们频繁地看到暴恐与反恐的发生。没有人可以从这个世界中抽离——“我和你都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苏力语)。暴恐,当然不是边疆的全部,甚至仅仅只是它展示给世人的一小部分,是中国这个伟大国家中很不好的那一小部分。然而,这些粗浅的经验和不完全的信息足以让我们去认真审视,边疆对于一个大国的意义和它的性质。
不无遗憾,至今为止,法学界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涉足甚少。国家的治边实践,既是一个宪政问题,也是一个在推进依法治国中如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这辑专号希望起到一点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推动法学界关注和研究边疆问题上有所助益。
四
这辑专号的面世要感谢各位作者。还要感谢很多人,特别是侯猛,在整个过程中,他付出了极大的心力。《法律和社会科学》按照专号确立主题轮流执行主编的机制,让我们这些散落在各地的青年学子,有了机会去尝试做一些学术推动和整合工作。感谢陈柏峰教授坚持组织“社科法学连线”对话活动,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这辑的“对话冯象”就有许多睿智的谈话,比如冯象教授说的要“小课堂和大课堂,两头抓”,成凡借《笑傲江湖》对学术界的评论,等等。
这是一个大有可为,又事事难为的时代,希望通过我们持续的、一点点的努力,为中国法学学术和法治建设有所贡献。
——————————————
[1]参见张剑源:《再造团结: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制度研究》,将由法律出版社2015年出版
附:本辑目录
第13卷第2辑 (2014) 苏力主编 王启梁 执行主编“边疆的法律”专号
论文
藏区的一妻多夫制/苏力
非“民族”的民族问题:黑树林水利纷争的人类学研究/嘉日姆几 石吓沙
这里没有普通话:藏区的双语司法实践/孙少石
“做工作”:基层政法的一个本土术语/易江波
评论
国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与边疆整合(1928-1949)/常安
治边西南: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张剑源
卷入“发展”的边疆民族传统与反抗/林叶
为什么要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李鲁岳
边疆与英国宪制的生成/王恒
对话
对话冯象:法学如何重新出发/陈柏峰 李斯特 冯象 成凡
编辑手记:被忽视的边疆/王启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