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位于浙东某市X县的山区小镇H镇,小镇总人口约3万人,四面环山,人们大多以种植茶叶和茭白作为主要生计来源。春节期间,村子里热闹非凡,但在与乡亲们的交谈中,我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象:许多处于五十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下年龄段的农民,谈论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农闲时节进城务工的经历。这一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奔波与奋斗,充满了机遇与挑战,也折射出时代发展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图景。
一、老年农民的季节性务工现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部分老年农民在传统务农的基础上,选择通过季节性进城务工提高家庭收入。
A是H镇Y村人,55岁,男性。其与妻子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26岁,小女儿24岁,均未婚。此前,A与妻子以种茶为生,两年前妻子离世,A经朋友介绍,与X县某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被派遣至X县某纺织厂工作,月薪6000元左右。
B夫妻同样来自H镇Y村,丈夫57岁,妻子53岁,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现已27岁,一个在外省某大厂工作,一个在X县工作。B夫妻在春、夏、秋三季忙于种茶,大约从五年前开始,每年冬季两人进城务工,在X县某装修公司从事相关工作,夫妻二人每月收入约1万元。
C夫妻是H镇Z村人,丈夫60岁,妻子57岁,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35岁,在S市工作,已婚并育有一子;小女儿26岁,也在S市工作。近十年来,C夫妻在春、夏、秋三季种茶,每到冬季,妻子会去X县做家政阿姨。
D夫妻也来自H镇Z村,丈夫63岁,妻子61岁,育有一子。其子35岁,未婚,在X县工作。春、秋两季,D夫妻在家务农;夏、冬两季,丈夫会去X县某装修公司工作,妻子则在X县或隔壁县的工厂打零工。
总体来看,在生产模式上,H镇五十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下的村民多采取“农业+非农务工”的复合生计模式,形成农业生产与临时性非农就业互补的生计结构;在地域范围上,该镇老年农民的务工活动高度集中于本县或邻近县域,体现出就近就业的倾向;在时间跨度上,非农务工普遍集中于冬季,与农业周期形成错峰,仅A因家庭劳动力短缺转向全年务工;在代际分工上,中老年群体承担兼业化的主体角色,其子女多已完成教育并进入城市就业体系,形成“父母务农+务工、子女城镇化就业”的代际分工格局。

二、老年农民季节性务工的成因分析
(一)农业收入的有限性与家庭经济需求
H镇农民在维持传统农业生产的同时,呈现出“亦农亦工”的就业特征,其本质是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以茶叶和茭白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具有显著季节性特征,劳动投入与收入周期存在明显时间差。这种生产周期不仅形成冬季近四个月的农闲空窗期,更暴露出传统小农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即分散经营的农户面对现代市场体系时,既缺乏规模效益,又丧失议价主动权。当茶叶集中上市导致价格波动时,个体生产者只能被动接受市场挤压,陷入丰产不丰收的恶性循环。自然风险的不可控性亦使得家庭经济安全如履薄冰,一次病虫害或极端天气或可摧毁全年收成。在此情况下,高额的教育成本和沉重的医疗负担所带来的家庭经济需求的持续膨胀与务农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形成双重挤压,迫使老年农民通过季节性务工降低收入风险。
(二)代际支持压力与家庭发展诉求
处于五十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下年龄段的农民作为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的重要成本承担者,承担着“上赡养下抚育”的双重责任。县域城镇化进程催生的住房刚需尤为突出,目前X县住宅均价约为1.3万元/㎡,购置100㎡住房需耗费家庭10~15年的农业收入。而附着于城镇住房的公共服务资源分配规则,更使孙辈教育质量与居住空间深度绑定,形成“购房-教育-代际流动”的传导链。除此之外,还有家中老人的医疗护理等一系列经济支出。在此过程中,老年农民的季节性务工不仅承担着收入补充功能,更为子代与孙辈的城镇化进程提供了信用担保。如B夫妻通过季节性务工获取的月均一万元额外收入,可显著缩短购房还贷周期,缓解子代购房的经济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代际支持已突破传统伦理范畴,演变为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的经济策略。
(三)劳动闲暇与灵活务工的时空契合
对于年过五十的农民来说,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经远超其身体承受能力。虽然其身体机能难以适应高强度工种,但却与城市服务业弹性用工需求形成互补。在劳动时间方面,装饰装修、家政服务等岗位的间歇性工作特征,与务农者晨昏作业的劳动惯习相契合;在技能迁移方面,农产品加工经验可以转化为食品厂分拣、包装等岗位竞争优势;在空间流动性方面,务工往往具有较为固定的工作时间,县域就业半径30公里内的日通勤模式,使务工者能兼顾田间管理与城市工作。由此,即可在获取农业保底收入的同时,获得务工增量收入,实现家庭总收入的最大化。
总结而言,农民季节性务工模式的形成,源于农业生产周期性与家庭持续发展的动力。老年农民作为家庭代际支持体系的关键支撑者,其季节性务工实质上是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经济压力妥协的产物。他们通过农闲时期灵活就业,规避了长期离乡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并且利用城市服务业季节性用工缺口,在有限的身体机能与市场需求间达成相对平衡,实现了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产业间的动态配置。

三、老年农民进城务工的保障机制
(一)土地保障:熟人社会土地制度的弹性运作
在农村地区,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更是老年农民进城务工的安全屏障。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其能够灵活配置土地资源,通过经营权流转、代耕代种等方式,节省田间劳作时间,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许多老年农民通过亲戚朋友、邻里关系等进行土地流转,租金普遍低于市场价。这种基于亲缘与地缘关系的流转,是熟人社会的互惠原则的体现。当务工受阻或项目结束时,农民亦可随时返回农村自主经营,形成可逆性的退出机制。
(二)资金保障:庭院经济的风险缓冲
对于老年农民来说,庭院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即便他们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务工,房前屋后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是他们经济安全的重要依托。A虽然在纺织厂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但他依然在家里种植蔬菜、养殖家禽,每年节省的生活开支可达近万元;B夫妻通过将空闲的房屋出租给茶商作为仓库获取租金收入,这笔额外收入与茶园的收益构成了家庭经济的双重保险。家禽养殖维系着节庆礼仪的乡土传统,闲置农房出租成为代际互惠的物质载体,这种由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不仅使务工农民避免过分依赖城市工资收入,还加强了其与家乡的情感联结,维系着村庄社会关系网络。
(三)劳动力保障:农忙与务工的时序协同
老年农民的务工模式往往与传统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紧密相连,通过灵活安排农忙和务工的时间,实现家庭经济的最大化。这种“三季务农+冬季务工”的模式,是H镇农民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实践。例如,C夫妻在寻找务工机会时,会尽量选择短期工作,以便能在茶叶的施肥季节返回家乡照料茶园。这种时间上的协调,使得老年农民能够在务工和务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不影响农业生产,又能在城市中谋得生计。此外,村民之间还通过组建劳务小组等形式共同应对劳动需求高峰,减少了单个家庭因缺乏劳动力而产生的困难。在务工时,依靠同乡间的互助网络,亦可共享工作信息、分摊交通成本。这种将农业周期嵌入城市用工节奏的实践,使老年农民在城乡间构建起弹性的时间链条,实现家庭总收益的最大化。

四、老年农民务工的价值维度
(一)自身技能积累与地位提升
与传统印象中的体力劳动者不同,老年农民工的技能积累正在逐渐打破人们对他们的刻板认知。以D夫妻为例,丈夫在装饰装修公司工作期间掌握了贴瓷砖、刷墙等专业手艺,如瓷砖的排版、粘贴技巧以及墙面涂料的调配、涂刷方法等,形成了可迁移的技术资本。这种资本具有双重适配性,在城市可对接标准化施工需求,在农村则转化为个性化服务能力。这些技能的掌握,让他在城市务工时拥有了稳定的收入保障。即便日后他不在城市的装饰装修公司工作,农村地区的房屋建设和翻新需求也一直存在,他仍然可以凭借自己所学的技能帮助乡亲们装修房屋并赚取额外的收入。而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民也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尊重,其社会评价标准不再仅仅以体力劳动的付出为依据,还增加了技术和手艺所带来的价值。
(二)重构农村家庭资源组织逻辑
老年农民进城务工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个人的经济收入上,还在于家庭资源的重构和再组织。过去,农民家庭往往通过一代代的物质和经验传递来维持生计,形成了线性、单向的资源流动模式。但随着老年农民走向城市,他们不仅将自己的体力劳动转化为城市需求的服务,还成为家庭资源流动的新枢纽。年轻一代可以借助父辈在乡村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优化他们的城市生活方式;而老一辈则通过子女的数字技能拓宽务工渠道。这种代际资源互通带来了城乡间的经验和资源互补,激活了农村家庭内部的复合型发展机制,从而使农村家庭在现代社会变得更加灵活、适应性更强,提高了家庭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三)养老模式转型与主体性重构
老年农民进城务工在减轻家庭养老压力、丰富其养老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务工收入为老年农民的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撑。在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中,老年人的经济来源往往局限于土地产出或子代的经济支持,而进城务工让老年农民有了更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增强了他们的经济自主能力,延长其自我养老的时间。另一方面,进城务工也为老年农民提供了丰富精神生活的契机。传统的农村生活主要围绕农业生产和家庭事务展开,进入城市后,老年农民有了接触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娱乐活动的机会,推动养老模式从原先的维持生存向发展性养老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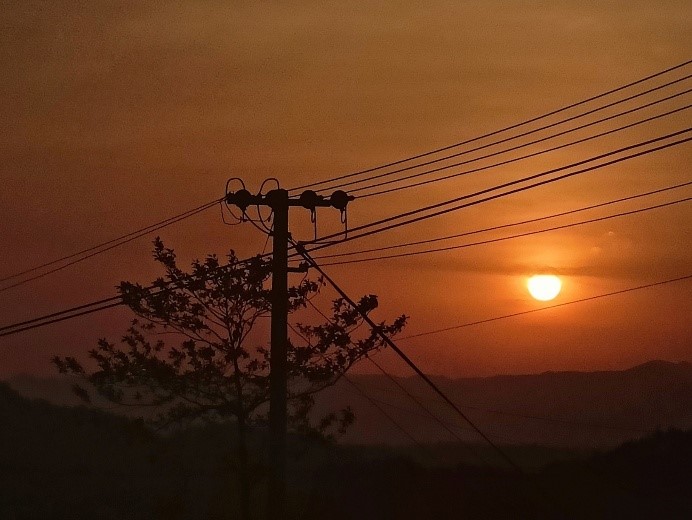
五、后记
五十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下农民群体的季节性进城务工经历,呈现出独特的生存智慧。他们通过灵活地调整务农和务工的时间安排,有效弥补了农业生产的空闲期,并利用城市务工带来的额外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缓解了代际间的经济压力。这些季节性城乡迁移实践不仅是应对生计的一种短期策略,也是社会变革的缩影。当城市开始尊重并吸纳乡村经验,当乡土智慧转化为现代服务能力,老年农民工不再是城市发展的剩余劳动力,而成为了城乡要素流动中的关键介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