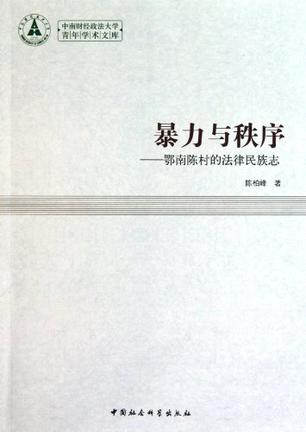中国法学要增强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力,既要坚持规范法律分析,也需要进行跨学科法律研究。跨学科法律研究的优势在于,尽管现代国家建立了学科划分制度,但在现象层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嵌入。由于学科壁垒仍然没有打破、相互联系较少,并且存在着诸多“空隙”,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就在于填补这些“空隙”,成为学科之间的联结点。在这个意义上,跨学科法律研究是能够联结法学与其他学科,在功能上也与规范法律分析相互分工。
陈柏峰博士的专著《暴力与秩序──鄂南陈村的法律民族志》,就是这样一次积极尝试。跨学科法律研究强调的是:第一,学术应直面社会生活实际、进入“田野”。法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建构法言法语、规范论证的循环体系,也不能仅仅关注“法律”问题,而应考虑如何解决好社会生活实际提出的问题。第二,法学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传统,必须要将其他学科的方法、知识引入进来。惟有如此,法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学问,而不是技艺。
在当代中国,关于乡村社会“秩序与法律”的研究成为热点。法学者与人类学者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研究分野。对于人类学者而言,在研究乡村社会时,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秩序的形成,法律仅仅是观察乡村社会的一个变量。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带着一种“无法”的观念进入到调查领域中去。而法学者则不然,同样是去做田野调查,但他们的观察镜仍然是法律,更关注“法律能否在乡村社会中实施”,关注基层司法。也正因关注角度和偏好不同,法学者更像是过去的“巡回法庭”,在获取必要的信息之后便结束调查。而不太可能像人类学者那样,要在乡村里长期“蹲点”了解其中的秩序过程。尽管法学者的这种调查方式受到质疑,这种质疑有其合理性,但也应当看到,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方法。法学者在进行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研究时,更多的是从国家法律观念出发,关注国家法律及其机构在乡村的意义。但乡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的确是“无需法律的秩序”,国家法律及其机构在乡村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是“一次性”的,因此,法学者花费的田野调查时间要比人类学者少。柏峰虽然是法学科班出身,但却从事了人类学意义上的长时期田野调查,因此,这部作品不仅弥补了法学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也是将法学与人类学研究打通的一个有效尝试。
柏峰的强项是他对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力,以及对鲜活实例的生动表述。这部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的实际,乡村纠纷解决的实际。他将陈村的纠纷大致分成三类:家庭内部的冲突、村民之间的纠纷、村民与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纠纷,对丧葬、风水、分家、家庭暴力、妇女自杀、外人等的分析都很有意思。他也讨论了这些纠纷解决的多元方式,但认为这些多元解决方式并没有呈现正常的分布状态,陈村的纠纷解决往往处在暴力(私力救济)与屈辱(无救济)之间。对法学来说,他的作品是纯粹和新鲜的,并且拓展了法学研究的视野。
不过,我与柏峰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有所不同。比如,他关注的焦点是乡村的纠纷解决,但在我看来,纠纷解决以及带有暴力和强制色彩的惩罚问题并不构成乡村法律民族志的主要部分,纠纷解决的背后其实是民间习惯。因此,乡村法律民族志研究的重心不是纠纷解决,也不是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民间习惯,而是纠纷解决之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习惯。又比如,他认为,跨学科法律研究应该超越反思。我倒是认为,在研究个案的时候,需要借助于既有理论的解释力,但正因为既有理论是具有普适意义的,而个案是地方性的,因此,通过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分析可以去发现理论解释力的不足,从而进一步修正既有理论,甚至可以通过研究中国的个案去颠覆一个西方理论的解释力。在这个意义上,反思也能够重建法律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此相关,我要批评的是,柏峰过于关注从中国经验出发、从实际出发来进行跨学科法律研究,特别是法律民族志研究,却没有去思考这一研究在何种意义上继承了人类学的知识传统问题。或许,这正是他试图摆脱西方理论“殖民化”奴役的一次“顽固抵抗”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开始关注到了法学的意义、跨学科法律研究的价值,我们正在朝着同一个学术目标努力前进。我们最需要的是,增进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增进对中国社会的整体理解。这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的、研究不同对象的法律民族志来完成。实际上,只要是基于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的田野调查和深刻描述,都是法律民族志。这意味着,我们所锁定的研究对象,不仅应包括中国乡村,也包括城市;既包括农村的民事习惯,也包括市场中的商事习惯;既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法律认同,也要关注法律人的法律认同。这些能够反映出中国社会法律民族志的全貌。因此,重要的不仅仅是个案的代表性,而是个案研究的深刻程度和抽象能力。如果能够完成这些不同研究对象的法律民族志,这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法治的理解,也有助于中国法学研究走出困境。
我与柏峰因文相识,最早拜读过他在《中外法学》上发表的论文“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之后,他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读博士,我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做博士后,又因为共同关注中国法律民族志而经常切磋。我欣赏他的才华。他是一位有学术追求的知识青年,对建立中国法学的社会科学知识传统抱有极大的热情。我想这份追求不仅是属于他的,也是我们这一代法律学人的。
侯 猛
2006年3月10日于北京大学承泽园初稿
2009年4月23日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静园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