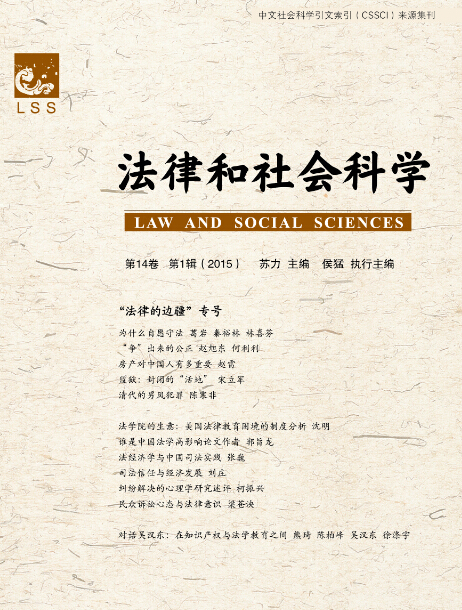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法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研究规则的社会科学,而非一幅可以直接用以指导司法实践的技术图纸。从事科学研究者的目的在于探寻真理,而从事技术实践者的目的则在于解决问题。就此二者不同的出发点论,笔者以为近来中国法学界有关“法律人思维”的争论[①]似乎都没有厘清“法律人”究竟指的是谁。质言之,法律研究者与司法实践者的思维或许本就应该有所不同,而将二者不加区分,笼统地给他们按上一种思维模式,恐怕并不合适。学者从各自默认的那部分法律人出发,主张这部分人应当具备的思维模式就是所谓“法律人”的思维模式,则无疑将陷入“关公战秦琼”的议论困境。
本文主要从司法体系的构造与运行条件出发,试图分析为何法经济学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没有风行,也不应当风行。基于这些分析,笔者认为教义法学仍应是中国法律实践者的首要思维方式。文章以下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答“什么样的司法体系更容易将法经济学的视角纳入司法实践 ”这一实证性(positive)问题;第二部分回答“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更(不)应该将法经济学的视角纳入司法实践 ”这一规范性(normative)问题;第三部分借助既有文献中的几个具体案例,简要说明法经济学的解释与法教义学的解释一样面临诸多困境。
一、实证性问题
针对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司法体系更容易将法经济学的视角纳入司法实践——笔者认为,从司法体系自身的特性来看,也许有两个因素值得重视,即对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 activism)的容忍与法官审判的独立性。
(一)对司法积极主义的容忍
在规范意义上,法经济学的政策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追求法律规则的效率。并且,在操作层面上,法经济学实际进行的是成本—收益分析,或者说是追求将蛋糕做得最大。因此,法经济学的视角要求司法裁判直接体现特定的政策追求,这无疑需要以司法积极主义的理念为依托。尤其当裁判涉及“难案”,无法直接形式地适用既有法律规则之时,效率导向的裁判是对政策问题的直接回应。基于这种特征,如果法经济学的视角要在司法实践中得以体现,那么,对司法积极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容忍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容忍一方面来自主权者,也就是说主权者能够接受司法机构的职能不仅仅限于对主权者设定的政策的消极执行,有些时候——至少在不明显违背主权者的既定政策的条件下——司法机构也可以积极推行其自身追求的某项政策。主权者的这种容忍能够避免由宪法性的、结构性的设计引起的司法失权,从而无法实现其政策追求。同时,容忍也来自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也就是说,在此职业共同体内存在一定的共识,即司法活动的功能不仅仅限于解决具体的纠纷,在一定范围内,司法活动还肩负着推行特定政策的任务。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这种共识直接决定着司法活动的第一线参与者是否愿意根据一定的政策目标,有针对性地确定诉讼和法律执行策略,从而在反复的尝试中推动这一目标的前行。假如缺乏上述内外两方面对司法积极主义的容忍,那么,司法实践恐怕很难直接且一贯地推进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效率作为这样一种目标,也就不会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青睐。不过,这种容忍显然只是司法实践接纳法经济学视野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二)法官审判的独立性
法经济学的视角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成本—收益分析,而这种分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针对个案的具体判断。一方面裁判者需要确定影响相关法律制度的成本与效益的变量,另一方面裁判者还需要估量在具体案件事实中这些变量可能的值域。换言之,要将法经济学的视角纳入司法实践,必然需要法官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行使相当程度的司法裁量。而法官进行司法裁量的自由度受制于司法体系的构造,尤其是法官作为个体在审判中的独立性。在司法权力趋于水平分布的司法体系中,法官的个体独立性比较强,或者说,法官的行动更接近于一个“本人”——而非“代理人”——的行动。最为重要的是,法官个体的司法行为及其结果不会成为司法体系评判其优劣并实施奖惩的依据。反之,在司法权力趋于垂直分布的司法体系中,法官个体的独立性比较弱——即便司法体系本身具有独立性。在此,法官的行动更加类似于一个“代理人”的行动,其司法行为及其结果会成为司法体系考评其优劣并给予奖惩的依据。尽管法官个体独立性弱未必表明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弱,但这两种独立性很可能是相联系的。并且,司法的独立性——无论个体还是体系——虽然可能与政体形态有相当关联,却未必完全对应。具体而言,集权制国家的司法独立性整体较弱,但在特定条件下,集权政体也可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司法独立[②],而民主制国家的法官和司法系统也可能受到相当的政治压力[③]。
在法官个体独立性较弱的司法体系中,法官的司法裁量会趋于保守,其行为将表现得更为厌恶风险(risk-averse)。这是因为裁量不仅影响到法官内心的满意程度——是否符合法官自身的口味,而且还会影响其面临的外部条件——包括薪酬、职位、名誉等。而司法裁量对这些外部条件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为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给法官带来的负效用(disutility),法官就可能寻求比较稳妥的标准作为其裁量的依据。因此,一方面法官会乐于寻求同行广为接受的标准而避免新鲜的标准,另一方面法官也可能更乐于接受裁量余地相对较小的标准。总体而言,效率标准既不是法律共同体传统接受的,同时——由于其不定性(indeterminancy)——也会带来更大的裁量空间。所以,法官个体独立性弱的司法体系更可能拒绝接受法经济学的视角。
(三)两方面的组合
也许有人会发觉以上提到的两个方面——对司法积极主义的容忍和法官审判的独立性——与Dama ka提出的司法行为的目的与司法权力的结构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密切相关。[④]的确,笔者的思路受到了Dama ka理论的强烈影响。一方面,以政策实施为目标的司法体系比以纠纷解决为目标的司法体系更可能容忍司法积极主义;另一方面,协调型的权力结构比科层型的权力结构更可能保证法官审判的独立性。照此分析,在表1中,最有可能接受法经济学视角的司法体系应该是第III类。
表1 司法的目的与权力结构(Dama ka 1991, p.181)
| 司法的目的 | |||
| 司法权力结构 | 政策实施 | 纠纷解决 | |
| 科层型 | I | II | |
| 协调型 | III | IV | |
不过,Dama ka模型中以政策实施为目标的司法强调国家权力对司法活动的影响,而笔者在此提出的司法积极主义更侧重于法官以及法律共同体以司法推进特定政策目标的实施。换言之,Dama ka的所谓的政策实施相对于司法体系而言可能是一种外生的目标,而本文涉及的政策实施更是司法体系中内生的目标。当然,如前所言,这种内生的目标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国家权力的容忍。因此,如果严格按照Dama ka的观点,那么,以政策实施为目的的司法体系也可能反而更不容易接受法经济学的视角——假如效率并非国家权力追求的政策目标。反之,假如效率是国家权力追求的目标,则以政策实施为目的的司法体系将较以纠纷解决为目的的司法体系更容易接受法经济学视角。不过,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假设之上的,而最重要的其他条件就是司法权力的结构。尽管以政策实施为目的的司法体系可能更易于接受效率的观点,然而,这种司法体系却往往会与科层型的司法权力结构相联系,而后者会抑制司法活动对法经济学视角的接纳。[⑤]
与外生的政策目标不同,在司法积极主义之下内生的政策目标由于没有外部权力的强制因素,更可能呈现相对多元的态势。也就是说,不同的法官追求的政策目标会有所不同,而法律共同体也可能认可多重政策目标的组合并存。于是,内生的政策目标中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效率追求。不过,虽然司法积极主义也会出现在科层型权力结构的司法体系中,但这种司法体系中的司法积极主义的程度通常会低于协调型的司法体系[⑥]。
在此,笔者要强调,本文仅仅试图从司法体系的特征中寻求影响司法实践吸纳法经济学视角的因素,但并非认为这些因素是充分条件。显然,除了司法体系的特征因素外,法律教育乃至文化传统等都可能影响法经济学视角在一国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四)中国的情况
在Dama ka的分析框架之中,中国的司法体系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第I类,即以政策实施为司法目的并以科层制作为司法权力的基本结构。[⑦]在这样的司法体系中,无论主权者还是司法机构本身都对司法积极主义抱有相当正面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不一定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所接受。中国法院展开的所谓“能动司法”运动正是这种态度的体现。[⑧]不过,迄今为止,虽然效率可能被作为司法机构内部运作的一个考量因素[⑨],却并未成为司法裁决中直接追求的一项目标。因此,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未普遍接纳法经济学的视角便不足为奇。然而,仅从对司法积极主义的容忍这一角度而言,法经济学视角进入中国的司法实践存在着胎动的可能性。尤其考虑到中国的整体政策导向倾向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效率目标在司法活动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并非不可想像。[⑩]不过,中国司法体系的科层制特征却可能是对司法实践接纳法经济学视角更加重要的制约。在中国目前严重结果导向的司法考核机制之下[11],法官总体的行为模式将偏向于厌恶风险和厌恶损失(loss-averse)。因此,他们更可能采取避免裁量和缩减裁量幅度的做法,以减少嗣后因不被上级认同的裁量结果而承受不利益。尤其是处在一个制度化程度低、面临各种外来压力的司法体系中,法官的行为将更加趋于保守。[12]正如上海的一位中层法官所言,中国法官的基本行为模式可被形象地称为“戴着镣铐跳舞”。[13]法经济学效率导向的分析视角,不仅与传统的公平正义司法观在直觉上形成突兀的对比,无论对社会一般公众,还是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而言都是一种新颖的概念,而且其分析方法也不为绝大多数法官熟知,分析结果也有着很大的不定性。所以,处于这样的司法体制性制约之下,很难寄望戴着镣铐的中国法官能在司法实践中迈出法经济学视角所需的新颖、大幅的舞步。[14]
二、规范性问题
针对前面提出的第二项问题——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更(不)应该将法经济学的视角纳入司法实践,笔者以为或许有三个方面值得考虑:法官的自制、国民对司法体系的认同,以及税收再分配机制的有效性。
(一)法官的自制
尽管法经济学的视角要求实施裁量,但这种裁量显然不应该是任意妄为的,或者以司法裁量之名行谋求其他利益之实。否则,不但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岌岌可危,也会引发司法体系自身的信任危机。无论是否接纳法经济学的视角,在一个成熟的司法体系中,法官对司法裁量都应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使自己的裁量不过份溢出于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诚如已故日本著名民法学家加藤一郎所言,即便法官以利益衡量作为裁判的直接线索,仍必须将由此得出的结论置于现行法的框架之下重新加以审视,假如利益衡量的结果与现行法的体系存在明显的矛盾,则应当放弃前者而重新审度利益衡量的角度[15]。这种对裁量结果进行规则正当化的过程同样也应该适用于运用法经济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这既是对法律规则稳定性的维护,也是对司法功能的自觉约束。就法经济学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而言,法官的自制十分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法经济学方法的不定性。这种不定性一方面体现在:就特定的法律规则规范的社会关系而言,影响其效率的变量往往多种多样,不同研究者通过选取不同的变量,可能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有学者认为,现实性与便益性应当成为分析选取变量的原则[16],但这两个标准过于抽象,恐怕难以付诸实践操作。例如,法经济学者对于权利救济的责任规则与财产规则效率优劣的莫衷一是,便体现出了这种因为变量选择不同而产生的理论的不定性。[17]另一方面,法经济学方法的不定性还表现为对于理论涉及的变量缺乏有效的测度标准,以致于理论的最终分析结论不定,其规范性作用也就无法确定。这方面的典型表现是在法经济学有关合同法的分析上[18]。此外,与这第二方面相关,即便有测度变量的合适方法,经验研究的方法不当也可能造成不定的结果,从而至少在找到正确研究方法之前给实践运用带来困惑。这方面的突出例证是有关死刑震慑作用的研究[19]。
面对以上各式各样的不定性,法官无论在选取模型、数据还是经验结论方面都会有相当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倘若没有基本的自制,很难避免法官在裁量过程中不参杂进其他不应有的考虑因素。在此意义上,即便在裁量中采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也仍有必要遵循最低限度的法律形式主义要求,至少裁量的结果不能与法律的文义发生明显的冲突。在强调司法独立,尤其是法官个体独立的司法体系中,这种形式主义的保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制。而这种自制又取决于长期的法律教育与法律文化的熏陶。要言之,本文所涉及的规范性问题的第一个命题就是:在法官整体缺乏自制传统的司法体系中,法经济学的视角不应被纳入司法实践。
(二)国民对司法体系的认同
国民对司法体系的认同是确立司法体系正当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国民才会愿意选择司法体系作为解决纠纷的途径,也才会愿意接受司法裁决的结果。在现代司法体系中,涉案当事人并未就特定争议事件适用的规则或者裁判的法官作出特定性认同,因此,对司法体系及其适用的规则的一般性认同就成为了司法体系发挥社会控制功能的合法性保障[20]。由此,司法体系的合法性得以确立,不再需要寻求当事人就各项规则和各名法官一一认同。对司法体系的一般认同使得裁判者得以根据其认为恰当的实体和程序性规则对案件作出裁量与判断。正是有了一般性的认同,司法体系的运作得以专业化和效率化。换言之,即便专业的司法活动依赖的具体规则不为当事人理解,规则适用的结果仍然能得到当事人的信任与执行。因此,越是专业化的司法活动,越可能无法得到当事人的特定性认同——因为当事人越难理解规则及其适用的原理,于是,这样的司法活动就越依赖国民对司法体系的一般性认同来取得合法性。遵循这样的逻辑,我们不难看到:司法专业化的推进,要以国民对司法体系的认同为基础,专业化程度越高,对这种认同的依赖也越深。
前面已经指出:法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给法官的裁量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同时,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高度的形式主义和抽象性——经济分析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模型化分析。尤其是当数学工具运用到法律的效率分析之中时,其专业化的程度大幅度提升,普通当事人对这种司法裁量的理解能力随之下降,取得其对司法活动的特定性认同也就变得更为困难。不仅是分析方法的专业化,法经济学以效率作为裁判追求的目标本身就较公平、正义这种司法裁判的目标更难获得当事人的特定性认同。一方面效率目标与人们对司法裁判理念的天然认识有差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效率是比公平、正义更具有专业内涵的概念,而这种专业性的内涵加深了普通人理解的难度。
正是由于法经济学的效率目标和形式分析方法具备高度的专业化,因此,司法实践在采纳其视角的时候尤其需要获得国民对司法体系的一般性认同。只有这样,当事人才能容易接受在不为其理解的具体规则运行之下得到的裁判结论。于是,本文有关规范性问题的第二个命题就是:在缺乏国民对司法体系的一般性认同的法域,法经济学的视角不应被纳入司法实践。
(三)税收再分配机制的有效性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效率都不会是唯一的目标,即便是主张效率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否认公平的价值,也有不少经验研究表明不公平可能削弱经济发展——至少从长期来看如此[21][22]。对于公平,法经济学者一般的观点是:法律体系——尤其是私法体系——不是实现公平目标的最佳机制,与之相比,税收与再分配机制能更有效率地实现社会认可的公平目标[23]。这种观点的基本理论依据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或者说是市场对于分配的中立性。假如我们同时认可公平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不仅是社会价值,也包含经济价值——以及税收再分配机制与法律体系在实现公平方面具有替代性——尽管前者或许在此方面更富效率,那么,就应当认为在税收再分配机制不奏效,不能肩负起实现社会公平的地方,依靠法律体系来实现公平目标就越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在缺乏最有效的实现公平的工具的地方,次优的工具越有用武之地。尽管对这种次优工具的运用也可能存在一个最优的限度,而且,在平衡状态,靠这种次优工具实现的公平也许在程度上要低于运用最有效工具实现的公平,然而,完全放弃使用次优的工具显然会令我们更加远离我们珍视的公平目标。
其实,以上的逻辑也可以通过经济学上简单的边际理论加以说明。如果将法律体系与税收再分配机制视为具有替代性的实现公平的方法,那么,其中一者发挥作用的程度越低,另一者的边际效用就越高。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本文所涉规范性问题的第三个命题:在缺乏有效的税收再分配机制实现公平目标的国家,法经济学强调的效率不应成为司法实践追求的主要目标。
(四)中国的情况
如果参照以上的三个命题,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目前不适于在司法实践中引入法经济学的视角。首先,中国的法官自制程度还很有限。一方面,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还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法律教育也有待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这些都使得职业共同体内的价值观念还比较纷杂。法官的来源虽然近年来已经变得较为专业化,但是,仍有相当部分法官——尤其是资历深的法官——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由于教育背景与价值取向的不同引起的职业文化的多元化,使得法官的自我约束,亦即第一方的控制(first-party control)[24]效果比较弱。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民粹因素却又很强大,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强烈。再加之整体腐败状况严重,法官也深受腐蚀[25]。这几方面的因素相互叠加,削弱了中国法官在进行司法裁量时恪守职业标准底线的动力。法官可能按照种种政治的、经济的需要,而非按照合理的法律逻辑进行裁量。实际上,自最高人民法院以降,目前中国的司法裁判不知其法源所本的已经比比皆是。[26]如果再允许法官添加上法经济学的效率目标,它就可能成为潜在的政治、经济影响的另一种体面包装。[27]其次,中国公众对司法体系还存在严重的不信任[28],而司法机构专业能力的加强并未改变这种不信任[29]。相反,由于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法院的公正性受到普遍质疑,司法的专业化很可能进一步令公众感到难以理解裁判的合理性,从而加深对司法体系的疑虑。如前所述,在缺乏国民一般性认同的司法体系中,裁判的正当性更加依赖当事人对特定裁判的特定性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前提就是能让当事人理解裁判依据的规则与法官推理的过程。高度专业化的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于拉近法院与当事人的距离,取得当事人特定性认同可能有害无补,从而使得司法体系更加孤立于国民大众,降低其制度上的重要性。
最后,中国现行的税收与再分配机制显然没有能够有效发挥调整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城镇居民——尤其是高收入居民——的隐形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重相当高[30],而这部分收入不纳入正式的收入统计,自然也无法成为所得税的计征对象。另一方面,中国现行的再分配体制严重不平衡,二次收入分配非但没有起到减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相反还可能促进了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譬如,养老、退休金收入的差距贡献了25%的城乡收入差距,成为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31]。对此,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提出了有名的“负福利”理论[32]。他指出中国的再分配机制未能给予低收入人群适当的福利,相反,却为部分强势集团创造了特权。前文已经阐明,在税收与再分配机制失效的地方,即使遵循法经济学家们的理论逻辑,也更应突出公平价值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而弱化对效率的追求。
三、法教义学与法经济学
(一)二者有无区别
本文以上的分析指出:基于中国司法体系的构造与运行条件,我们不应提倡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一观点的一个衍生结论是:至少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司法实践者主要应采用教义法学的思维方式。那么,到底有没有教义法学的思维方式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比较教义法学者的主张与法经济学者有关法律适用的主张是否有所不同。假如二者确有不同,就很难否认在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之外别无教义法学的思维方式。对此,笔者以为二者至少有两点重要区别。其一,二者对法律目的及其实施结果在法律适用中扮演的角色认识不同。其二,二者对成文法文义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认识不同。首先,教义法学并非不考虑法律的目的,不体察法律实施的后果,以法律目的为出发点的教义法学解释方法屡见不鲜[33]。不过,其与法经济学体察目的、结果的区别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教义法学对目的、结果的考察处于补充性地位,唯当法律文义不明,且无法从法律内在体系释明文义之时,方才考虑目的及适用结果的合目的性。反之,于法律文义清晰,可直接通过三段论适用时,则目的问题不会在法律适用中彰显出来。不仅如此,教义法学考察法律适用的结果是否符合法律的目的往往并非贸然行事,而是有一个试错演变的过程。譬如,日本民法第177条有关不动产物权变动不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并未对“第三人”的范围直接加以限制。由此,日本法院早先的判决也未对此作出限制。直到民法典施行10年之后的1908年方由当时的日本最高法院参酌法律为保护“对于主张登记欠缺具有正当利益者”之目的,而将“第三人”的范围加以缩限,以将侵害不动产权利的侵权人排除出去[34]。
与此相对,在法经济学的思维中,目的追求是第一位的,具体而言,就是追求效率是法律的首要——若非唯一的话——目的。因此,在法律的每一次适用中这一目的都要彰显出来。同时,对于多数法经济学者而言,效率这一目的几乎是先验的,因为正如Coleman所言,法经济学者并未就为何效率应当成为法律追究的目的作出有力的说明。[35]而既然这一目的是先验的,那就不存在发生错误的问题,于是,在法律适用中对此也没有试错的必要。
另一方面,相对于法经济学的效率一元论,教义法学考虑的法律目的更加多元,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公平。对于公平,法经济学者一般的批判意见是其含义模糊不明。但是,即便公平含义不明,也不能否定公平是与效率不同的一个目的——假使法经济学者认为效率含义明确,那么,公平的含义不明正好体现其与效率的不同。况且,含义不明也不足以否认公平可以成为具有道德哲学(deontology)支撑的法律之目的。
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对于公平作为法律目的最为大胆的否定是桑[36],其以进化论的观点认为“效率和公平是一回事”。[37]然而,这种将公平与效率等同起来的观点不无疑问。其一,假如进化要求公平与效率趋同,那么,经过进化得以留存的社会,其法律甚至其他的制度规范也应该趋同——因为效率之外别无其他进化选择的条件,而效率又是有统一确定的含义的。事实显非如此,不用比较现存的经济发达社会与欠发达社会的法律制度,即便同等发达的德国与英国,其宏观法律制度有显著分别,这已是法律人的常识。从具体微观的法律制度论,甚至同属大陆法系,又同样经济发达的德国与日本,差别也可谓俯拾即是——如物权变动的要件。并且,在法经济学者看来,这些制度差别的确具有效率差别。[38]其二,即便承认进化的最终结果可以令公平与效率合二为一,也同样无法否认进化过程中这两者仍旧可能分别。由于进化过程的漫长,这种分别更可能长期存在。我们也无法知道当下的人类社会究竟处于进化的哪一环节,所以也无法遽然承认当下的公平与效率观已经是一回事了。其三,纵使我们已经处在公平观进化的终点,也无法否认公平与效率可以不同,因为在统一的效率观念之下同样可以出现不同的规则选择,而当对一种规则的选择明显多于其他规则时,指引这种选择的就只能是效率以外的其他目的。这方面的经典例证是对终局博弈(ultimatum game)的实验性研究[39]。尽管在此类博弈中,从博弈人角度看符合效率要求的金钱分配方式多种多样,可是接近均等的分配方式则明显受到博弈人的青睐。基于以上三点理由,笔者无法赞同公平与效率合二为一的观点。
最后,在说明教义法学与法经济学的第二项区别之前,笔者想强调:教义法学对法律目的的考察并不必然排斥效率,而只是认为有比此更加重要的目的,即公平正义,假如两项目的发生冲突,则效率或应让位于公平。[40]
教义法学与法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区别还在于二者对文义在法律适用中的地位认识不同。在教义法学看来,法律文义不仅是解释的起点,也是解释的归宿。为此,一方面,在对法学的宏观认识上,教义法学突出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分野,解释论绝不可超越文义许可的最大范围,在此范围之外的法学理论则属于立法论的范畴。尽管法律的文义无可争议地具有模糊性,但对其核心含义人们也同样无可争议地存在相当共识——否则语言文字即无法达成人际信息交流地基本功能。正如“指鹿为马”,人所不齿。教义法学在此方面的实践,譬如,日本民法上曾经存在抵押权涤除制度,无论学界还是司法、金融实务届均将其诟病为损害抵押权人利益的祸水,或是“无用之累赘”。纵使如此,在法律修正之前,日本法院从未径行否定涤除的效力,而是采取了根据法律文义尽量缩小其适用范围的做法。其中一个具体的例子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涤除权人包括所有权、地上权或永小作权的取得者,而判例对于让与担保已采担保权说,故而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将让与担保权人排除在了涤除权人之外[41]。及至2003年日本民法典修正,绵延百余年的涤除制度方才寿终正寝。
另一方面,在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微观认识上,教义法学强调文义解释的首要地位和最终约束力,借此构筑起一套解释原则。即便在进行漏洞补充时,也要依据文义判断确为立法之缺失方可补充。并且,漏洞补充这一司法行为本身也需要有法律的文辞作为基础,如台湾地区“民法”第1条,瑞士民法第1条等[42]。即便是教义法学中最为激进的利益衡量学说,也强调衡量的结果必须能穿上法律的外衣,假如的确无法穿上这件外衣,则需要放弃衡量而非法律[43]。此外,教义法学还定下了诸如“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等规则限制法官脱离文义、过度裁量。
与教义法学重视文义的地位不同,法经济学重视的是法律适用的后果是否符合效率。在此意义上,假如根据文义适用法律无法满足效率要求,则文义本身是不足以成为对法官裁量的拘束的。由此,法经济学的思维在本质上不存在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分别。于是,在身处普通法系的法经济学者看来,是否严格遵从先例成为了法院的信息成本是否大于当事人的交易成本的问题[44]。而桑在论述允许撤销赠与合同的理由时,显然也将《合同法》不允许经公证的赠与合同撤销的规定抛在了一边——既然能以最低成本避免事故的一方不会因为公证而改变,法律在此作出区别性规定便是不符合效率的,从法经济学的立场上看,这条法律就是应当修正的。[45]
以上论述表明教义法学与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确有不同。归根到底,教义法学比法经济法学更加强调法律适用的形式,而法经济学则比教义法学更加注重法律适用的结果。也可以认为前者更注重司法的程序正义,后者则更注重司法的实用效率。在有长期教义法学传统,概念法学观念盛行的国家,法经济学确实有助于缓和法律的僵化,避免法律人在司法实践中过度重视细节,而忽略全局。但中国当下的情况却很不相同,我们长期忽略程序的重要性,而惯于追求实用。非但普通国民的认识如此,即使受过专门法律教育的人士也难幸免。有鉴于此,突出强调教义法学思维在司法实践中作用,对于逐步形成中国的法治传统意义不可低估。一则教义法学的思维有助于培养法官形成司法自制的意识,二则其强调公平正义在司法中的地位也更能赢得普通国民的认同。
(二)法经济学指导司法实践有无优势
提倡法经济学思维者以为教义法学方法老套,所谓教义,实为托词,因此不足以指导司法实践。而法经济学则从“理性人思维”出发,为疑难案件的审理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那么,法经济学的思维是否确实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这种优势呢 以下同样运用桑论及的几个具体案例,对此问题加以考察。[46]1、赠犬撤销案
桑引用国内学者的著述,认为允许撤销赠与合同的教义法学理由是“权利义务相一致”,然而,这一理由无法说明为何《合同法》不允许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撤销。同样,英美法的“对价”理论也无法对此加以解释。因此,教义法学的这些理论概念仿佛都成了“事后的正当化说辞”,而非“事前的判断依据”。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桑在此提出的问题,从教义法学的立场上看,并非一个司法实践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因为《合同法》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只需依法执行即可,也非所谓“难案”的情况。只有站在法经济学抛却法律文义的立场上,才可能让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有关司法实践的问题——文义不足凭,效率价最高。
那么,教义法学是否无法自圆其说呢 笔者无法就国内学者的观点一一查证,但日本的教义法学者对此给出的理由则有所不同。通说见解认为之所以非要式赠与允许撤销,而要式赠与不许撤销,是因为形式要求有助于避免当事人的轻率行为[47]。这种理论不但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与现实法学大家Fuller对对价的功能解释[48]不谋而合,可见教义也可以是尊重法律功能价值的。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桑对此的法经济学解释又是不是托词呢 这一解释认为受赠人对赠与承诺的误信可以被视同一场事故,因此能以较低成本避免这场事故者就该负担事故的损失。
“尽管双方避免事故的预期成本在个案中无法比较,但法院却会推定:让Y提高些警惕要比让X改变自己随意许诺的生活习性更容易一些……这一推理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上像X一样随意许诺的人数量众多,而像Y一样粗心大意的人却很罕见。并且,将责任分配给粗心大意者可以使法律‘树敌较少’,由此降低法律的管理成本。尽管一律执行赠与承诺,可以减少谎言和欺骗的数量,但由此产生的少量社会收益补偿不了极度攀升的执行成本;相反,拒绝粗心大意者的索赔请求却可以抑制诉讼的动机,减少诉讼的数量,降低法律的实施成本。此外,既然法律应该鼓励人们去成长,就不应过分保护那些天真无邪的人们。毕竟,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欺骗的世界,这是法律无力改变的既定社会条件。”[49]
这一段引文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如随意许诺者多而轻信人言者少,减少谎言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执行成本的攀升,我们生活的社会充满谎言——却未提供具体的经验证据作为支持。由此,其可以依凭的大概只有人们一般的直觉印象了,可这和教义法学求助人们普遍的公平观又有何区别 况且,这里的一些观点恐怕很难赢得人们基于直觉的普遍赞同,也可能与经验证据不符。比方说,由于我们生活的社会充满谎言,所以我们应该允许撤销赠与合同,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伴随一个社会谎言数量的减少,我们就该看到不同的法律规则了。如果以社会信任度作为一个社会谎言多少的测度,中国和日本在此方面区别不小[50],但有关赠与合同撤销的规则却为何别无二致
此外,假如法经济学真的关注效率,那么,引文的观点恐怕也难以符合效率要求。首先,放任社会充斥谎言将令信息辨识成本(verification cost)激增,逆向选择问题恶化,增加交易成本,从而抑制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是为何法经济学分析赞同教义法学拒绝欺诈合同效力的原因[51]。其次,即便一方的注意成本低于另一方,但只要双方的注意都可能降低事故的概率,就降低事故的成本这一效率目标而言,让一方完全负担事故责任而另一方完全不负担责任(即采用无责任过严格责任规则)通常是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这也是对事故责任法进行经济分析的一个共识性结论[52]。最后,抑制谎言是否会增加诉讼数量从而增加法院的执行成本呢 答案也可能是否定的。在诉讼成本高于和解成本的条件下,理性的当事人只有对诉讼结果抱有不同的期待方才会选择诉讼,否则应该和解。因此,诉讼数量往往不取决于法律规则的内容如何,而是法律规则的清晰程度[53]。所以,除非有理由认为抑制谎言法律规则必然不如放纵谎言的规则清晰,否则诉讼数量未必因为规则内容变化而变化。
假如法经济学的衷心在于效率,其利器在于经验而非直觉,那么,根据笔者的以上分析,桑站在法经济学立场上,为论证允许赠与合同撤销而提出的这一系列观点或许也不得不被视为托词——言不由衷的表述——了。
2、致电司机案
桑提到的司机因行车过程中接听电话而发生事故的案件,在主张法经济学思维的学者看来,其实是因果关系与过失认定应当合二为一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借助边际汉德公式认定某一行为具有过失,那么,该行为就应被视为事故的法律上之原因。[54]这种将因果关系虚无化的倾向自Calabresi以来对侵权法的经济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5]。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边际汉德公式本身只有在假定了某些事实因素是事故的原因这一前提之下才得以成立的。简言之,因果关系的认定在前,汉德公式的运用在后,两者原本不是一回事。在经典的侵权法经济分析模型中,基本的目标函数可以被写作min p(x)A + wx[56] 。其含义为:侵权法的目标是将预期的事故损害与预防事故所需的成本之和最小化;其中预期的事故损害等于事故发生的概率p与一旦事故发生损害的规模A之乘积,而x则代表了会影响事故发生概率的诸因素。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选取x——而不选y或者z进入此目标函数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因果关系的判断,而这种判断是不依赖于目标函数的——这个函数对选取的任何变量都适用。因此,这一经典的法经济学思维实则隐含了因果关系判断独立于过失判断,却被误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同时,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到,经济分析方法并没有给因果关系判断增添任何新的武器——它完全没有涉及这一前置于过失判断的问题。因此,美国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Robert Cooter教授才会认为:因果关系的认定根本上是涉及自由(liberty)的问题而非适用经济分析的效率问题[57]。
以致电司机案为例,比方说,为什么不将汽车制造商的注意程度纳入目标函数呢 假如汽车制造商改变设计,屏蔽车内的通讯信号,不是可以降低事故概率吗 对此,持法经济学论者也许会说:因为改变设计的成本很高。但是,这只是回答了根据边际汉德公式,汽车制造商不因被认定有过失的问题,而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汽车制造商根本不被纳入该公式考量的问题。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存在能以最低成本减少事故概率的行为人,也不等于仅仅让此一人采取行动是最有效率的——其他行为人可能不如该行为人那样能低成本地降低事故概率,但其采取降低事故概率的行动的成本仍可以在边际上低于由于这种概率的降低而带来的收益。换言之,就是即便我不如你能降低风险,也不等于我什么也不该做。我该做还是不该做,以及该做些什么要依据边际汉德公式确定。而将我的行为完全排除在该公式考虑的变量范围之外,则等于预先假定我是什么也不必做的。由此可见,法经济学思维方式对于因果关系的处理不见得比教义法学多一些理智,少一分武断。
说完了因果关系,我们再来考察过失认定方面法经济学的思维是否较法教义学更有优势。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法经济学确实为我们找到了一些重要的分析变量,有助于厘清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过,这一优势或许更多体现在理论认知上,而非司法实践上,因为司法实践不仅需要找到变量,还需要将这些变量可操作化(operationalize)。而可操作化就包含了如何测量变量的值,假如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法官即使知道了变量也只能跟着感觉走,顶多是猜测一番罢了。与教义法学相比,区别只是从猜测合理之人会如何行为,[58]变成合理之人行为的成本—收益如何。这正是本文以上提到的经济分析不定性的一个体现。况且,严格说来,法经济学采用的上述目标函数是针对具体行为人的具体情况而定的,而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合理之人的标准,因为效率的最终评价依赖于纯粹主观的效用(utility)标准。因此,在效率指引下往往产生权利应如何归属不确定的情况[59]。这样一来,实际上在缺乏客观度量的情况下,法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恐怕比法教义学的思维方法要求裁判者作更多的猜测——后者猜一次就够了,而前者则每次都要猜。
最后,还应指出:在过失判断问题上,“合理之人会如何行为”与“合理之人行为的成本—收益如何”完全可能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非如桑所言,法官必然——至少是下意识地——在做成本—收益比较。法官权衡的也可能是其他有关公平正义的因素,例如行为人是否从造成损害的行为中获得利益。实际上,例如《合同法》第406条有关受托人注意义务的规定就考虑了类似因素——虽然委托合同是否有偿本身不会改变受托人避免事故发生的成本。
3、小鸡啄眼案
此案同时被法教义学的支持者与法经济学的支持者引用[60],双方对如何处理此案的结论并无不同,争论似乎仅仅在于用谁的思路得出这一结果更加合适。不过,双方均没有说明判断这种“合适”与否的标准是什么,而只是各自在各自思维体系下推导出同样的结论来,因此,自然也不可能说服对方自己的这一套思路更好。
从教义法学的思路出发,孙认为法律对于是否应当抵销未成年受害人之监护人的过失规定不明,但从立法本意旨在考虑加害人与受害人的利益关系平衡出发,应当对法律进行扩大解释,从而将受害人的过失扩大到受害人一方的过失。同时,孙也指出,这种解释是具有实际上的法律依据的,即最高院的一则司法解释。[61]因此,以最高院司法解释作为司法实践中具有完全约束力的渊源(authority)论,则教义法学的这种解释毋宁已经成为单纯的依文义适用法律而已。此外,笔者还想补充:假如认为在此法律规定确实不明,那么,还可以依比较法解释方法得到同样的结论。《民法通则》第131条的规定非但与日本民法第722条第2项内容类似,而且二者在民法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亦类似,均位于有关侵权损害赔偿中免除或减轻责任的条款之中。[62]可见二者应具有相当的可比性,而日本民法第722条第2项的解释早就将“受害人一方”包含在适用过失相抵的对象之中[63]。由此,就教义法学论,得出此等结论完全合适。
持法经济学论者对上述解释理论的攻击实质是:其以解释之名掩盖求助目的、结果之实。笔者以为,这种批判并不恰当,原因是如前所言,求助目的、结果并非法经济学的专利,早在法经济学诞生之前,法教义学就已经接受了考察法律之目的,权衡适用之结果来解释法律。目的解释、目的性扩张等等均是教义法学的标准方法。具体就本案涉及的扩张解释而论,法教义学者也不讳言其“亦有目的上之考虑”[64],又何来包装掩盖之说呢 如前所述,究其实质,教义法学与法经济学的分歧主要不在是否要考虑目的、结果,而在什么目的、结果。持法经济学论者将法律的目的全部归结为效率,而教义法学者则会考虑其他目的——尤其是公平。因此,桑认为孙所谓“达到某种平衡”必然走向成本—收益分析,其实并不尽然。例如,这种平衡也完全可以是在矫正正义意义上的:让无过错的被告承担责任不符合矫正正义[65]。需要指出的是:从行为人过错出发的矫正正义与效率目的并不必然吻合。譬如,严格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符合效率要求,但却未必总能得到矫正正义的支持[66]。
持法经济学论者完全依赖成本—收益比较,认为由受害人一方采取注意以避免事故的成本低于由动物饲养人一方采取注意的成本。因此,应当让未尽注意的受害人一方承担部分损害。假如忽略法院为判决过失相抵而增添的额外成本,那么,这种经济分析大体也是合适的。[67]问题在于:持法经济学论者并没有证明受害人一方的注意成本必然低于动物饲养人的注意成本。这一点恐怕也很难严谨证明,因为不仅如前所述,注意成本因人而异,而且会因为外部客观条件而异[68]。在本案中,比如养了几只鸡,地方多大,孩子是男是女,母亲是老是少,等等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于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论最终也是依赖于一般的直觉印象,这与教义法学用以判断过失的合理人标准(或者矫正正义的观念)求诸一般直觉印象的做法并无多少实质区别。
最为可惜的是,双方在探讨这个具体的法律适用——区别于法律规定的理由——问题时,恰恰都弄错了应当适用的法律。本案若发生在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则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7条。因其明言“由于受害人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故而并无《民法通则》第131条适用之余地,理由是特殊规则优于一般规则适用。对于此,相信法教义学者应无异议,而持法经济学论者,除非全然不顾法律文义,一味推行成本—收益分析,否则,也应可以认可。于是,若案件于此期间发生,则双方均会认可免除养鸡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假如此案发生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则应适用该法第78条,于是,除非养鸡人能证明受害人一方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其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在此,受害人一方的故意似乎无从谈起。不过,究竟何为重大过失 笔者似乎既未见到教义法学者的说法,[69]也没发现法经济学者的标准。[70]倘若双方都不能为养鸡人找出个说法来,恐怕法律适用的结果就要让双方一同失望了。
从以上对小鸡啄眼案的评论,我们似乎看不到教义法学的思维与法经济学的思维有谁更胜一筹:在双方擅长的领域,各自都有一套说法,而这套说法依据的都同样是不怎么精确的直觉印象,况且最终双方的结论也无不同;反过来,对于困难的问题,双方又同样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而当双方代表在畅谈法律人思维方法的时候,似乎都弄错了适用的法律。
四、谁的法律思维 (代结论)
在讨论法律人的思维问题之前,或许我们先应该厘清“法律人”说的是谁 笔者以为:从事司法实践者的思维方式与从事法律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可以很不相同。前者不仅需要可行,更需要合法。可行指的是在司法实践者的教育背景下,可以被他们普遍掌握;合法指的是司法实践者的裁判方法能够得到作为司法活动对象的民众的普遍接受。从这两个条件出发,本文认为司法实践者——尤其是中国当下的司法实践者——主要应当采用教义法学的思维方式。一方面,法学教育仍是以教义法学为主要内容的。这不仅是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也是大陆法系各国以及英国的现状,甚至也是法经济学发韧之地美国的现状。[71]要求司法实践者以法学院没有系统传授过的法经济学思维来判断案件,恐怕不切实际。当然,或许可以认为法学教育本身也可以改革。但是,如果改革的目标是让从事司法实践工作者普遍掌握经济分析的思维方法,那么,也许需要将法学院全面改造成应用经济学院才行。笔者不敢预言这种改造计划有多大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以公平正义作为司法实践的目标,以形式逻辑为这种实践的基本表现形式,更加符合普通民众对于司法应有之意的认知。教义法学纵然有概念黑箱,但至少这些黑箱被用公平正义包装起来了,而这种包装比法经济学赤裸裸地提倡效率,似乎更可能赢得民众的认同。显然,一项根本改变民众认知——由偏爱公平正义转向偏爱效率——的社会革新恐怕过于任重道远了。无论如何,如果要建设真正的法治,我们的任务是更多地强调程序的重要性,而非短路地考察结果。如前所述,这一法治建设的要求与教义法学而非法经济学的思维愈加吻合。
简单否定存在教义法学的思维也不仅合理。一则,如前所述,教义法学的进路确实与法经济学的进路有所不同。二则,即便两者确有共同的思维模式,例如形式逻辑的推理过程,也不足以认为教义法学的思维不存在。譬如,物理学与现代经济学都运用了数理逻辑的思维方式,但这显然不等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就被物理学的思维吸收掉了。再以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看,即便美国也不会直接选择经济学家来当法官。而如果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才是正宗的法律人思维方式,那么,法官的最佳人选就应当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应用经济学家了。
当然,司法实践会面临许多无法通过简单的文义解释或者逻辑推演直接解答的问题。对此,教义法学也承认目的和结果考察的作用。此时,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都可以为司法实践作出贡献。而这种贡献主要是提供知识——亦即基本可靠的事实——而非思维方式,更不应该代为设定目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其他各学科可以提供多种食材、佐料,但烧什么菜,烧成什么味道,仍然应该由教义法学来掌勺。实际上,例如统计学就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知识,但法官本身并不需要掌握统计学的技术或者思维方法。
与司法实践者不同,法律研究者既不必受制于教育背景的局限,而研究基本也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毋宁说,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研究者应当打破学科的界限,探索各种可能的接近真理的思维方式。实际上,跨学科研究已日益成为当下各个领域学术研究的共同特征,法学研究自然也不应例外。然而,学术研究——尤其是科学性研究——的任务首先是揭示真理,而非推行某种价值观。因此,严肃的科学研究应当谨慎对待规范性问题。同时,切实掌握教义法学的内容与思维对于从事法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同样有积极意义。毕竟,假如法学研究者丧失了“法学的”知识,或者我们的学科丧失了基本阵地,那么,我们又能为跨学科研究做些什么呢
最后,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教义法学者与法经济学者确实应当加强沟通,深入理解各自的工作,而非片面地相互否定。记得Cooter教授曾言:“先知道法经济学是什么,再来批评法经济学!”我想这句话也应当同样适用于对待教义法学的态度。
*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电子信箱:fredericklily@gmail.com。本文部分内容取自笔者2014年6月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第四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法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①]朱苏力:“法律人思维 ”,载《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14卷第2辑;孙笑侠:“法律人思维的二元论——兼与苏力商榷”,载《中外法学》2013年25卷第6期;桑本谦:“‘法律人思维’是怎样形成的——一个生态竞争的视角”,载《法律和社会科学》2014年第13卷第1辑。
[②]大革命前的法国是有名的例子,参见Doyle, William. “The Parlements”, in Keith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 1):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 Oxford, UK: Pergamon Press, 1987;有关皮诺切特治下智利的例子,参见Hilbink, Lisa. Judges Beyond Politics in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Lessons from Chil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有关自民党治下日本的例子,参见Ramseyer, J. Mark and Eric B. Rasmusen, Measur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udging in Japa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④] Dama ka, Mirjan R. 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Legal Proce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⑤] Dama ka就曾明确指出:科层型权力结构的司法体系更容易排斥结果主义的司法标准以及实用主义的推理方法(Id.,pp.21-23),而法经济学显然是建立在结果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上的。
[⑥]有关日本的司法积极主义,参见Itho, Hiroshi. “Judicial Review and Judicial Activism in Japa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53: 169-179 (1990).
[⑦]尽管在中国条块结合的政治权力结构中,不同层级的法院和法官可能受到多重本人的制约,但就单个的法院或者法官而言,其处于科层结构中一定层级的地位并无本质改变。当然,由于多重本人的出现,代理人的行为以及各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会有所变化,这已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有关中国的条块政治结构,参见Lieberthal, Kenneth.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NY: W.W. Norton & Company, 2004, Chapter 6;有关多重本人的官僚结构,参见Tullock, Gordon. 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 New York, NY: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5, Chapter 9;有关在多重外部制约下司法机构满足自身偏好的条件,参见Cooter, Robert D. The Strategic Constit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ter 9。
[⑧]关于能动司法的一个典型例证,参见杨艳辉诉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上海民惠航空公司客运合同纠纷案,(2003)徐民一(民)初字第1258号(法院判决后主动向被告的行政主管机构发出司法建议书,提出行业性的整改建议)。
[⑨] Zhang, Taisu.“The Pragmatic Court: Reinterpreting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China”,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25: 1-61(2012).
[⑩]譬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也曾响彻全国。
[11] Minzner, Carl.“Riots and Cover-ups: Counterproductive Control of Local Agent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1: 53-123(2009).
[12]近年来,中国的司法体系不仅受到既有的政治压力(参见Peerenboom, Randall.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还日渐受到媒体以及民粹主义(populism)的影响(参见Liebman, Benjamin. “Watchdog or Demagogue The Media 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Columbia Law Review 105: 1-157 (2005). Minzner, Carl. “China’s Turn Against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9: 935-984 (2011).)。
[13]笔者与上海某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访谈,2013年7月4日。
[14]本文并不否认中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局部的创新冲动(参见Stern, Rachel E. “On the Frontlines: Making Decisions in Chinese Civil Environmental Lawsuits”, Law and Policy 32: 79-103 (2010).),不过,这种冲动背后的激励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并且,从现有经验证据看,这种冲动依然是个别性的,可能主要存在于某些具有强烈晋升欲望和一定晋升潜力的法官中间。此外,司法创新本身也不一定意味着法官乃至司法体系挣脱了镣铐,获得了自主性,因为创新仍可能因循特定的外部压力(参见Liebman, Benjamin. “Malpractice Mobs: Medic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Columbia Law Review 113: 181-263 (2013).)。
[15]加藤一郎:《民法における論理と利益衡量》,東京:有斐閣(1974)。
[16] Jackson, Howell E., Louis Kaplow, Steven M. Shavell, W. Kip Viscusi and David Cope, Analytical Methods for Lawyers (2nd ed.), New York, NY: Foundation Press, 2011.
[17]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有Kaplow, Louis & Steven Shavell, “Property Rules Versus Liability Rules: An Economic Analysis”, Harvard Law Review 109: 713-790 (1996). Ayres, Ian and Eric Talley, “Solomonic Bargaining: Dividing a Legal Entitlement to Facilitate Coasean Trade”, Yale Law Journal 104: 1027-1117 (1995). Bebchuk, Lucian Arye. “Property Rights and Liability Rules: The Ex Ante View of the Cathedral”, Michigan Law Review 100: 601-639 (2001). Ayres, Ian and Paul M. Goldbart, “Correlated Values in the Theory of Property and Liability Rul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2: 121-151 (2003).
[18] Posner, Eric A. “Economic Analysis of Contract Law After Three Decades: Success or Failure ”, Yale Law Journal 112: 829-880 (2003).
[19] Donahue, John J. and Justin Wolfers,“Uses and Abuses of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e Death Penalty Debate”, Stanford Law Review 58: 791-845 (2006).
[20] Shapiro, Martin. Courts: A Comparative and Political Analysi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21] Persson, Torsten and Guido Tabellini,“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600-621 (1994). Keefer, Philip & Stephen Knack, “Does Inequality Harm Growth Only in Democracies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323-332 (1997). Halter, Daniel, Manuel Oechslin and Josef Zweimüller, “Inequality and Growth: The Neglected Time Dimen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 81-104 (2014).
[22]不过,对此也存在相反的证据,参见Forbes, Kristin J.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869-887 (2000)。
[23] Kaplow, Louis and Steven Shavell,“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 ”,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3: 667-681(1994). Kaplow, Louis & Steven Shavell, Fairness Versus Welfa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Cooter, Robert D. &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6th ed.), New York, NY: Pearson, 2012.
[24] Ellickson, Robert C. 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 Li, Ling.“Corruption in China’s Courts”, in Randall Peerenboom (ed.),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China: Lessons for Global Rule of Law Promo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6]任举一例,最高人民法院允许银行在对其客户违约的案件中仅仅承担补充责任(见枣庄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柴里煤矿诉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青岛保税区华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案,(2009)民提字第137号),而无论是《合同法》还是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违约者可以承担补充责任的规定,法院的判决书也完全没有引用相关的法律条文。这一做法似乎也为各地法院接受,如上述最高院再审案件的一、二审判决(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05)滕民初字第2716号、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枣民四终字第105号))。同样,即便是侵权责任,中国现行侵权法律也没有规定银行侵害客户财产权可以仅承担补充责任,而法院却又会不知所据地作出这样的判决(如信达投资诉浦发银行长宁支行财产损害赔偿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高民五(商)终字第22号)。
[27]波斯纳法官也曾类似提到形式主义司法更易于抵制权力干预,因此更加适合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不过,笔者在此着重突出形式主义司法更容易令非法的裁判因素——包括政治干预、经济贿赂等——被察觉(桑本谦也有类似观点),而对形式主义司法是否真的足以抵制政治权力并无确信。波斯纳法官还指出中国的法官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因而不能胜任以实用主义为皈依的法经济学分析。笔者认为这一因素进一步增加了法官自制的重要性——面对缺乏经验的工作,更需要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在裁量中采取自我克制的态度。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以及大陆法系其他地方的职业法官制度与其司法体系的科层型权力结构或许有密切关系——科层结构制约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内人才的平行流动,譬如,有经验的律师很难进入司法体系从初级法官做起,而直接在科层体系中取得中、高级地位又与科层制的内在逻辑不合,最多只能是例外情况。参见Posner, Richard A. Lecture to the Students in the Summer School in Law and Economics, July 12, 2012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8] Liebman, Benjamin. “Malpractice Mobs: Medic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Columbia Law Review 113: 243(2013).
[29] Gallagher, Mary E. “Mobilizing the Law in China: ‘Informed Disenchan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Consciousness”, Law & Society Review 40: 783-816(2006).
[30]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http://mcrp.macrochina.com.cn/u/54/archives/2010/203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3月31日。
[31]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收入差距报告”,http://chfs.swufe.edu.cn/upload/shourubupingdeng.pdf,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3月31日。
[32]秦晖:《共同的底线》,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版。
[33]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梁慧星:《民法解释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版。
[34]内田貴:《民法I総則 物権総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版,第445页
[35] Coleman, Jules L. “The Grounds of Welfare”, Yale Law Journal 112: 1511-1543(2003).
[36]桑本谦:“‘法律人思维’是怎样形成的——一个生态竞争的视角”,《法律和社会科学》2014年第13卷第1辑。
[37]此前,即便最为彻底否认公平之于法律之价值的Kaplow, Louis and Steven Shavell, Fairness Versus Welfa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也承认公平与效率不是一回事。
[38]研究与法系相关的效率差异的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 Robert W. Vishny,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 1113-1155 (1998)已成为重要文献。有关物权变动要件产生的效率差异,参见Miceli, Thomas J., Henry J. Munneke, C.F. Sirmans & Geoffrey K. Turnbull, “Title Systems and Land Value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45: 565-582 (2002).
[39] Guth, Werner, Rolf Schmittberger & Bernd Schwarze,“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3: 367-388 (1982).
[40]在此意义上,教义法学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而正如Coleman所言,道德哲学家并不认为福利或者效率不应成为法律的目的,只是不认为其应该是法律的唯一目的,参见Coleman, Jules L., “The Grounds of Welfare”, Yale Law Journal 112: 1538-1539(2003).
[41]张巍:“日本的抵押权涤除制度”,载《民商法论丛》2002年第24卷。
[4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页。
[43]加藤一郎:《民法における論理と利益衡量》,東京:有斐閣(1974)。
[44] Cooter, Robert D. &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6th ed.), New York, NY: Pearson, 2012, p. 93-94.
[45]桑本谦:“‘法律人思维’是怎样形成的——一个生态竞争的视角”,《法律和社会科学》2014年第13卷第1辑。
[46]桑本谦:“‘法律人思维’是怎样形成的——一个生态竞争的视角”,《法律和社会科学》2014年第13卷第1辑。
[47]内田貴:《民法II債権各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版,第158页;近江幸治:《民法講義V 契約法》,東京:成文堂1998版,第119页。
[48] Fuller, Lon L. “Consideration and Form”, Columbia Law Review 41: 799-824(1941).
[49]桑本谦:“‘法律人思维’是怎样形成的——一个生态竞争的视角”,《法律和社会科学》2014年第13卷第1辑。
[50] Edelman, 2014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at http://www.edelman.com/insights/intellectual-property/2014-edelman-trust-barometer/about-trust/global-results/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3月31日。
[51] Cooter, Robert D. &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6th ed.), New York, NY: Pearson, 2012, p.361.
[52] Brown, John P. “Toward an Economic Theory of Liability”,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 323-349(1973).
[53] Priest, George L. & Benjamin Klein, “The Selection of Disputes for Litigatio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3: 1-55(1984).
[54]桑的表述略有不同:“在漫长的因果链上,只有那个在事先看来成本最低的环节或至少是成本合理的环节,才可能被认定为与事故的发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过,可以看出其要旨在于通过汉德公式确定令成本最小化的行为方式。
[55] Calabresi, Guido. The Cost of Acciden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56]Brown, John P. “Toward an Economic Theory of Liability”,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 323-349(1973).边际汉德公式其实就出自这一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
[57] Cooter, Robert D. “Torts as the Union of Liberty and Efficiency: An Essay on Causation”, Chicago-Kent Law Review 63: 523-551(1986).
[58]教义法学目前对过失的认定主要采用客观的合理人标准,参见王利明:《民法》(第5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7页;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内田貴:《民法II債権各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版,第314页。
[59] Cooter, Robert D. “Torts as the Union of Liberty and Efficiency: An Essay on Causation”, Chicago-Kent Law Review 63: 545-547 (1986).
[60]孙笑侠:“法律人思维的二元论——兼与苏力商榷”,载《中外法学》2013年25卷第6期;桑本谦:“‘法律人思维’是怎样形成的——一个生态竞争的视角”,载《法律和社会科学》2014年第13卷第1辑。
[61]最高院就法律具体适用问题有权作出解释,此点在我国法律实践中概无疑问。
[62]此种体系位置并非大陆法系民法的通例,参见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第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页。
[63]内田貴:《民法II債権各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版,第405页。
[64]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65] Dobbs, Dan B. Law of Torts, St. Paul, MN: West Group, 2000, p.15.
[66] Id., p.16.
[67]在此,桑不知为何没有像在“赠犬撤销”案中一样考虑诉讼数量增加导致的法院执行成本增加。显然,判决过失相抵与判决严格责任相比,法院的在每项诉讼中的裁量成本将增加。同时,由于过失相抵规则比严格责任规则更具有不确定性,也会增加诉讼的数量。
[68] Shavell, Steven. “An Analysis of Causation and the Scope of Liability in the Law of Tort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2: 463-516(1980).
[69]例如,张对重大过失的定义仅仅是“疏忽”与“轻信”之前加了“极度”二字而已,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不过,王提出了违反一般人的注意构成重大过失的见解,参见王利明:《民法》(第5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7页。
[70]传统的汉德公式显然是不考虑过失是否重大的。至于其他法经济学文献,就笔者所知,似乎也未有涉及。原因也许是在法经济学最为发达的美国,恰恰法律不认为重大过失(gross negligence)对侵权责任有何特殊影响,参见Dobbs, Dan B., Law of Torts, St. Paul, MN: West Group, 2000, p.349.
[71]笔者曾有幸就读于哈佛和伯克利两所美国法学院。其间,笔者修习的所有部门法学课程——包括财产法、担保法、公司法、合同法、版权法——都是以传统的案例教学——相当于大陆法的教义法学——为主要授课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