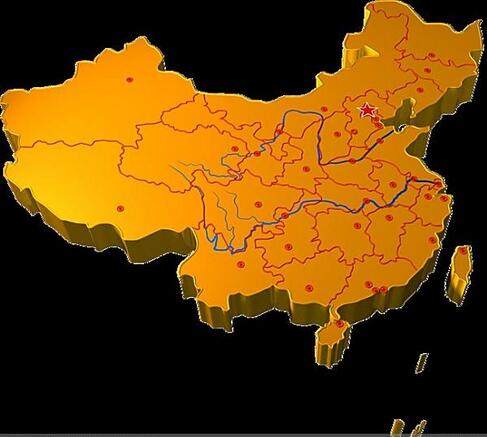☆:文章正式发表的文字与此略有差别,如需引用,请参考正式版本。
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工作报告中说:“在经济活动领域内,一些干部……把法律当成保护本地区局部利益的工具。……如果法院判决本地应偿还外地的债务,就不高兴,就指责法院‘胳膊肘往外拐’;甚至阻挠法院对一些案件的受理、判决和执行。”这是第一次在国家最高议事议政仪式上提出地方保护主义话题。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以上现象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报告中被正式称谓为“地方保护主义”。[1]自1988年开始到2001年的历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都批评“地方保护主义”对法院审判、执行的干预。对当代中国民商事审判进行观察的西方学者,在审判不公、法官滥用权力的归因上,亦多认为系出于体制所导致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local protectionism)。[2]对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批评,逐渐演化为一种控制性话语形态,成为主导1990年代末启动司法体制改革以来,直到晚近,对中国司法政治治理进行重构的基本叙事。
从地方保护主义叙事形成迄今三十年,已沉淀出一个可进行感知的较完整图像,从而使得对地方保护主义话语形态进行评析,成为可经验检验、测证的事件。本文从地方保护主义发生的制度结构切入,试图表达和论证以下事实:地方保护主义叙事来自于1990年代初期之前的印象。1992年后,剧烈的变革所产生的制度外部性,使得地方党委、人大、政府,进行地方保护主义的激励和所享有的支配力不断衰退;从当事人的案件收益、寻租成本、搜寻成本以及各项风险量值来分析可清楚的判知,并非地方党委、人大,而是上级法院,是当事人寻求对案件进行干预的优先选择,持续三十年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叙事遮蔽了该事实。对于司法改革这一总前提的厘清、查勘,是司法改革政策设计再出发的起点。
一、司法地方保护的初始发生条件
“地方保护主义”的语义所指,在三个词语关系项的背景下获得界定:⑴“中央—地方”关系内,先地方,后中央;强地方、弱中央;⑵“地方—地方”关系间,一地阻隔、封锁另一地,以邻为壑;⑶“条条—块块”关系中,作为地方的块块利益优先,条条中的上级被抑制。由于在中国,“中央”和“地方”,基本的指涉为党委之间的关系,“条条—块块”关系中的“块块”,指涉为地方党委、人大、政府,所以这三个词语关系项,在以法院为讨论主题时,具体表现为:⑴县委/区委—市委/地委—省委—中央,在这一梯级内的地方下级党委,对于利益获取,优先于上级党委,尤其是中央之上;⑵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将本区域的利益置于同级其他地方所辖区域之上;⑶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强调本地政治经济社会利益,将本地政治、经济、社会后果的最优结果实现作为至上,排斥本级法院的上级法院、最高法院的规范性要求。
最高法院批评的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中的“地方”,显然非虚空的地理所指,也不是普通百姓手持铁锹“暴力抗法”,而是指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因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叙事的基本外延,是在前述“地方保护主义”三个词语关系项的第一、二种的部分形态和第三种形态内。在具体的发生因果上,地方党委、人大、政府三个机构各自具有不同权力,对地方法院的事务介入,表现方式也不同。以学院内的视角来看,1980年代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发生来主要自于两个方面:
(一)“无利不起早”,地方党委、人大、政府有利益激励。这种激励,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方向:外在激励,在非归属于官员私人利益的公共事务的职务责任上,与当地公共利益有密切的一体连带关系;内在激励,在个人私利上,与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有个人亲缘或其他非公共的私人性交往,基于该当事人请托或贿请,而出面干预个案。
(二)地方党委、人大、政府之所以能对地方法院发布各种指令,是因为地方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两类主体之间因单向的“支配-顺从”关系,司法被迫偏离,具体表现为:法院的组织任免受制于地方党委和人大,编制、人事受制于地方政府;法院的财和物,包括工资、经费以及审判庭、法庭“两庭”建设等,受制于地方政府。
将以上促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益激励和支配关系,置于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中,在具象的、真实发生的语境内,一一铺陈开进行分析可见,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当时的“司法”和“地方”两个方面的宏观、微观状况,面对“保护主义”,或无力抗拒,或有其发生根由。
首先,在郑天翔院长批评地方保护主义的1980年代中后期,经济背景是所有制结构上,除东部极少量外资成分的企业外,经济主体的基本形式是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查1986年4月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拟定时所依据的经济数据得知,1985年底,全国工业企业46.32万个,全民所有制的9.37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36.78万个,其他所有制占0.17万个。[3]地方党委、政府,作为本地国营经济的产权管理人、资产的具体代表人,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制度义务。在计划体制“一盘棋”的既定政策,和当时法院干部的业务素养、审判水平下,如果地方党委、政府对法院审判、执行,不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关注,反而可能构成玩忽职守。其次,以1980年为界,至1993之前,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由“一灶吃饭”改为“分灶吃饭”,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实行多种形式的包干体制,[4]因此,地方党委、政府尽可能留利地方,不让肥水外流。
其次,因实行单一制经济主体、管制经济、票证经济、单位制,加之人口较少流动等因素,纠纷极少,法院刑事之外的业务基本只以解决婚姻、家事和简单民事纠纷为主,也并无现代西方将法院作为对行政机关等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法院在政权内的分量极其轻微。以法院为专门的治理机制,而设计区别于政权内其他机关之外的单独的审判人员任命和人财物体制,意义微小。
再次,除两个激励方向和两个支配手段之外,另曾有两个背景纵深因素曾对地方保护发挥作用:1、在郑天翔院长作报告的1986年,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总体规模极为微小,调整商事关系的规范网格极为稀薄,整个民商经济方面的实体法,除简陋的57个条款的《经济合同法》之外,基本空白。2、计划经济年代,物资调拨、资金划转等,都由地方政府通过各局、委、办,依照上级计委下达的计划统一调度。1985年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正从计划经济,向“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体制处于剧烈的调整时期。地方政府在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时,方式、手段上,进退失据。如对于银行贷款无法收回,1987年前,多是银行与主管局委,通过行政手段扣款解决。当异地法院以借款为案由介入收贷,尚未试点体制改革的地方政府会认为这是反制度行为。[5]
二、初始条件的变化
以上制度状况以1993年为转捩点,发生根本性变化。[6]随着法院被赋予的处理经济、社会事务的力量增强,对法院的治理也渐列入单独序列而别于其他机关。
对于利益激励第一个方向的外在激励:首先,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中央和地方财政区分税种和比例分别征管,[7]不同企业的当家税种不同,对于地方的利益不同。2012年“营改增”后,地税更加萎缩,地方政府以留税留利在地方为目的进行地方保护的冲动衰减。其次,1997年中共十五大后进行大规模国有企业改制,各地政府“抓大放小”,剥离、重组后的国有独资和国资控股的企业占地方企业数量巨幅减少。[8]目前各地,除中央企业在本地分、支公司之外,地方国有企业数量比例较此前已极小,少数保留的国企都是本地利润表现优质,呆坏账、拖欠等诉讼纠纷较少的企业。
对于利益激励第二个方向的内在激励,即个人私情、私利上,中共中央逐步建立了严格的地域回避、避籍任职制度,以切断党政官员与地方的人情、利益联系。1995年,中共中央规定“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十年的,必须交流;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不得在原籍任职。[9]2002年之后,一方面将避籍任职范围扩大,另外,由于人口流动,因父籍而发生的本人籍贯意义衰微,所以将几类重要干部的避籍任职改变为“本人成长地”回避。[10]因普遍异地做官,周末和节假日地方党委、政府大院空巢,以及党政官员听不懂本地方言,成为政坛新现象。本地诉讼当事人与本地党政领导层极少有深厚的、无法扯断、无法躲开的亲缘关系。
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第二个方面,即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及于地方法院的“支配-顺从”力量,尤其需细分出个项辨析。对于“人、财、物受制于地方”,这句成为成见的表述,细致拆分后的形态如下:
(一)“人、财、物”中最重要的“人”,分为组织任免、编制、人事三项事权。
首先,组织任免。地方各级法院干部的任免,是一种多重的条块耦合结构。由于法院事实上是行政首长院长负责制,所以上级党委对院长任免的决定权,在法院内部管理上是最高支配权力,本级地方党委对副院长级干部的决定权,嵌套在上级党委对院长决定权这一前提内。激起地方保护的案件,通常较为重大,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合议庭提交院长主持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基本上消解了承办人、庭长、主管院长这些由地方党委、组织部管理的干部承受的压力。
其次,编制。地方法院编制原由地方政府管理,法院增编、用编需向地方政府人事部门申请。1982年之后单列中央政法编制,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组织部等把政法机关编制“从国家机关总的行政编制中划分出来,分别单独列为国家公安编制、司法编制和检察编制。实行统一领导,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级管理。”[11] 1988年设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此后历届编委主任均由总理担任。1991年升格为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中央编委),其常设办事机构中央编办单列为正部级,机构性质“既是党委的工作部门,也是政府的工作部门”,权威度增强。[12]地方各级法院编制由中央编委统一领导。法院增编,层报中央编委、编办批准,仅编制内用编,报地方编办核准。[13]地方政府人事部门的权力进一步弱化。
再次,人事。地方法院新进非领导职务的普通法官,原由同级地方政府人事局派遣,“法院想要的人进不来,法院不想要的人顶不住”。[14]2004年后,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初任法官,一律实行省级统一招考,考试录用由省级党委组织部主管。基层法院、中院的进入计划报高院,由高院统一审核汇总,报省级党委组织部审批,统一向社会公布。考试由省级党委组织部会同高院组织实施,考务工作由省级人事厅考试中心统一组织考试,分数线由高院商省级党委组织部确定,拟录取名单经高院审核,报省级党委组织部审批。[15]市、县、区各级地方政府人事局对于法院招考、录用处于无权状态。
(二)“人、财、物”中的“财、物”部分,其实际形态也已发生巨大流变,并非西方观察者所想象的一笼统地估堆式由法院所在政府财政拨款,而是区分类别,区分财政级别,根据“财、物”内容的不同种类,分别由中央财政、省财政和法院所在的市、县财政分级进行保障,保障原则也不同。中、基层法院所在的同级政府的制约力下降。[16]
此外,立法供给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构成这两个因素,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起点,也迅速变化。首先,在加大法律供给,提高法院自组织能力上,1993年后,以民商事、经济为立法中心的各级立法腾跃,到2010年底,“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17]中国司法过程中,另有巨量的司法解释和批复、纪要等非正式规范发挥着规范作用。以政策、原则为遮蔽,实际注入地方个体利益的干涉,日益遭遇到成文立法的阻遏。其次,1992年后,各级政府经历了1993、1998、2003、2008四次大规模的机构裁减、合并、职能下放,直接管理经济的纺织、商业、冶金、轻工、电子等部、委、局、办,裁撤合并完毕。地方政府通过这些职能机构直接介入经济流转的具体手段衰弱。
综上所言,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对于本地法院审理的案件利益“保护性”介入,经过二十年的制度改新,较之郑天翔、任建新院长时代,驱动已极大衰微,支配力也巨幅衰落,来自地方政府的制约大部消散,地方党委、人大有支配力的制约亦仅在在副院长以下的干部任命上。当然,在权力的毛细血管层面,目前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各种潜在的激励和具有的支配,也依然丝丝缕缕。但是,如由此作为出发基点,对地方保护主义进行单线一维的制度主义独断,漠视了人是处于行动中,而非被教室黑板上板书、幻灯片标绘的模式图所设定。当事人借重地方党委、人大提供“保护”,的确是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形,但只是情形之一,而现实中有多种可能作为备选,如果寻求其他手段,付出的成本,获得的收益,以及行为风险量值,都小于前者,那么地方保护主义就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备选项,而非行动中的人的必然选择。
在实践的发生中,制度逻辑上的激励因素和支配,落入现实的复杂的司法场域后,呈现出的外观是:寻求案外干预的当事人优先选择的是寻求上级法院,“地方保护主义”常处于被“存而不论”的境地。
三、司法地方保护发生的可能方式
地方保护主义的断言,是以非个体论的视域来看待法院和地方党委、人大、政府,但是黯淡了任何组织都是由有着现实利益盘算的个人构成。诉讼中的行为由人实施,被纳入地方保护主义这一主题进行分析的行动中的人有:诉讼当事人、地方党政官员、受理案件的法院法官、上级法院的法官。成熟的、会算计的人,不会因为一个空的指号——大家都在本地工作生活,仅因为这种非理性的情感性因素,而幼稚地“保护”激烈对抗的各方当事人中的本地一方。以此视角,对地方党委、人大、政府介入法院审判,进行仔细打量,可将“地方保护主义”分为三种类型:
类型Ⅰ:地方党委、人大主管负责人,出于职务职责担当所系,基于社会公共政策、政治需要考虑,对法院某个案件做出指示;
类型Ⅱ:地方党委、人大的某些官员,收受一方当事人贿赂后,转以组织名义对案件进行介入。
类型Ⅲ:地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或者公安、检察院等其他政法机关的官员,因在职务交往中,与法院的院长、庭长、普通法官建立了熟人关系。受一方当事人委托,利用脸熟,向审理案件的法院出面请托。此种类型中,彼此的职务关系,只是一个“由头”,仅起到居间、搭线的桥梁作用,实质介入案件起作用的是贿赂。司法实践中习惯将此称为“管闲事”、“说情”。因行为可能构成受贿罪(间接受贿、斡旋受贿)、关系人受贿罪、介绍贿赂罪、徇私枉法罪或至少是违纪,彼此均讳莫如深,案卷中完全不留痕迹,外界更难以知悉。
对以上三种介入,法院自身的各种报表、各项统计数据中,没有列项,也难以统计,外来的观察者更无从有实证的数据来证实或证伪立论。但是,作为一个精于计算的公务人,每个官员都会对自己行为的成本、收益和风险量值进行精算。具体情况包括:1.组织获得收益、私人支付成本的行为,个人没有激励去实施;2.私人支付成本、私人也获得超出边际成本的收益时,个人才有激励去实施;3.如果是组织支付成本,私人获得收益,个人具有最大激励。
以此作为分析工具,来看这三种类型。
类型Ⅰ,如果仅是当地企业获得保护,而官员个人没有超出的好处,但却要担负来自政治上的责难,导致政治前途黯淡,那么,没有官员会去行动。作为公务人,官员的目标是晋升。如果自己的公务行为并不有利于晋升,反而需要官员支付私人成本、职务风险,遭致政治上的降级和责难,那么官员没有任何动力去实施。
类型Ⅱ,与类型Ⅰ在外观上相同,都是启动组织程序,或利用职务,公开地打招呼,而不是私底下贿买法官。但这两种方式在诉讼中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原因是这两种方式在诉讼中有着极高的被发现概率。第一种以组织名义正式介入案件,方式是党委、人大办公机关启动草拟-审核-签署-传递公文流程,最后发送于法院,对应的法院办公机关收文-呈送-会签-下发审判庭,而不会是“一对一”两人交易于密室。第二种没有正式公文,只是党委、人大负责人的批示或电话交代。对此,司法实践中历来的做法是,将批示附入案卷的副卷;如果没有书面指示,仅是电话通知或会议协调,则由案件承办人写一个备忘纪要,由合议庭、审判庭相关知悉人共同签名,附入副卷内,以资凭证。
但是,与党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事务不同,法院处理的事务是诉讼,而诉讼由对立、冲突的控辩双方构成,法院只是一个裁断者。因此,诉讼不是封闭的、信息密不透风的单方内部审核,而是由势不两立、剑拔弩张的冲突对抗中的当事人与法院三方构成的多重互动关系。在持续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推动下,中国民商事诉讼的职权主义已弱化。出自法院职权、导致诉讼情势中双方当事人的任何细微颤动,都会被情势不利的当事人所迅速感受到。如果承办法官个人没有在党政领导“打招呼”的案件中获得较大个人私利,那么法官为避免追责和将矛头对准自己,多会以确定的或晦明的,哪怕是点到为止的方式将领导批示这一信息,明示、暗示传递给另一方当事人,以为自己卸责。
由此可见,如果地方党委、人大以组织方式介入争议中的诉讼,偏袒一方当事人利益,将导致该事实被对立方当事人牢牢的抓住,诉诸于更高党委、人大机关、媒体舆论的救济。而实践中,能够牵动地方党委、人大,以组织名义介入的案件,必定是重大标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均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量。即使是地位极低下的当事人,也会以“弱者的武器”方式进行越级上访、信访、自媒体形式的网络攻击,从而导致地方党委、人大官员个人政治上的不利。所以,类型Ⅱ和类型Ⅰ,尤其是类型Ⅰ,主要发生在近年流行的官场小说中,司法实践中并不常见。
类型Ⅲ,并非出于公心,而基于个人利益,通过私密、隐蔽的利益勾兑、权力贴现方式,介入、干预诉讼,这两种方式,不是郑天翔院长所称的地方保护主义。这种没有职务制约关系,而是通过贿赂搭桥的情形,与地方党委、人大的职权对于法院的支配关系无关,任何能够与法院的承办人、庭长、主管院长等人实现权力互惠、利益互换的人,包括地方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公安、检察院的官员、私营企业主、有支付能力的任何布衣乡民,都可以以此方式涉入案件。对司法冷静的观察,获得清晰的认识:案件裁断结果发生不正常的偏差,必然是货币或可兑现为货币的非现金收益方式在进行支配,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脸熟”、人情面子在起作用。只要能够支付购买审判权力对价的任何人,有能搭上线的渠道,即可能实现贿买目的[18]。诉讼实践中表现出的情状,确如马克思所说:“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地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9]
因此,即使通过司法结构变动,法院彻底独立于地方,不管是省级以下统管或最高法院垂直统一领导,还是法院原子式的独立,都无法排除贿买行为。反而是,人财物独立于地方,只能更加增大法院与这些官员、老板、资本拥有者私底下进行权力贴现、勾兑、创租时,法院一方的筹码和收益,对于改变法院、法官徇私枉法没有任何撼动。因此,进入本文讨论主题的只有类型Ⅱ和类型Ⅰ。但由于类型Ⅱ和类型Ⅰ在外观上无法区分,所以,必须从内容上再进行界定。类型Ⅱ虽然不是郑天翔院长批评的那种地方保护主义,但是,因为其一方面利用对法院的职务制约关系,另一方面个人收受贿赂,非常具有隐蔽性,这被认为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发生形态,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从驱动力上看,类型Ⅱ地方保护主义的发生,是一方当事人游说、捕获了地方党委、人大的官员。对于当事人而言,其目的是要通过贿买党政干部和法官,改变不利于自己的诉讼,在一起零和博弈(zero-game)的诉讼中,一方当事人预期自己败诉,因此寻求贿请外部干预诉讼,改变不利处境。如果行贿后,实际诉讼支出少于预期败诉损失,即:法院实际裁决的支付数额,加上行贿的成本开支总和,少于预期败诉损失,那么当事人就会有激励选择贿买。对此进行公式方式计量表达式为:当事人贿买诉讼的最后所得=(预期败诉损失数额—法院裁决支付数额—行贿成本)>0。对此进行简单换算:
第一步:(法院裁决支付数额+行贿成本)<预期败诉损失;
第二步:[诉讼收益(预期败诉损失—法院裁决支付数额)-行贿成本]>0。
该公式的文字意义为:只要当事人通过贿买(bribery)介入诉讼的预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EU(B)>0,也就是法院裁断结果,可以少支付或不支付,当事人就会有动力去贿买党政干部和法官,即EU(B)=(诉讼收益-贿买成本)>0。
在诉讼实践中,贿买的具体的基本形态是:1.当事人先搜寻到合适的官员,贿买该官员,该官员同意出面请托对法院有支配力的目标官员。2.目标官员向法院打招呼,要承担政治名誉损失,另有被追责可能,因此当事人必然以支付贿金方式,弥合该官员的显在和潜在损失。3.即使当事人贿买了高级别的目标官员,在由法院具体审判执行时,必须再向法官具体的相关人行贿。当事人完成这一流程,有两次大的跳跃:首先,搜寻到目标官员,支付了对价,目标官员同意向法院“打招呼”,官员“打招呼”的有效性如何,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继而,因为贿买官员和法官行为是犯罪行为,一旦被查知、追诉,带来人身自由丧失和案件收益丧失的双重后果,必须评估自己行为败露的风险,如果风险稍大,即使有收益,不足以启动贿买司法行为。这两次跳跃,实际是双重风险,其中任何一次风险发生,都将导致当事人的贿请支付行为失败,没有收益。所以,细化当事人的成本-收益表内的各项指标为:1.成本包括:搜寻官员需要支付的成本;贿买官员需要支付的成本;贿买法官需要支付的成本;2.诉讼收益是当事人从案件胜诉获得的直接收益;3.风险量值为高度不确定值,数额可能为0~∞,0为无风险,∞为无穷大。
因此,在引入风险量值后,公式换算后为EU(B)=(胜诉收益-贿买成本)-风险量值>0,进一步贴合当事人采取实际行动的心理估算进行考量,当事人通过贿买介入诉讼的预期效用的心理行动路线,用以下公式表达:EU(B)=(胜诉收益-搜寻官员成本-贿买官员成本-贿买法官成本)-风险量值1-风险量值2>0。
四、司法地方保护发生的低可能性
拆解前述公式,对当事人的成本-收益表内的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如下。[20]
(一)搜寻成本
批评地方保护主义主要剑指基层,即县区和市。中国政制下,在一个市、县、区中,能对法院进行批示,要求法院汇报工作,从而正当介入司法的制度角色有3-5位。因为中国法院80%的一审案件由县区基层法院受理,因此,为节简表述,以基层法院所在的县为例,能合法介入司法的制度角色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作为常委的政法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会主任、分管内务司法/法工委工作的人大常委会会副主任。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会分工负责”的要求。[21]副书记职数削减,不再有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和同时担任纪检委书记的副书记以及分管组织、分管协调等工作的副书记,除作为副书记的县长之外,仅有一位协助书记、负责统筹协调的副书记。在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会主任的县,能通过组织方式介入地方法院,并对案件做批示的只有4位:书记(人大常委会会主任)、副书记、作为常委的政法委书记、分管内务司法/法工委工作的人大常委会会副主任。在区、市、省一级,虽然级别不同,但有支配力的官员数量大致保持不变。
对于司法政治的这种形态,部分作品的认识有偏差,认为地方政府序列内的官员经常干预司法。实际上,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下,地方政府不可能对法院采取组织方式的干预。原因在于:
首先,中国政体架构是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法院与政府平行,所以政府序列内的官员,无权以组织方式介入法院案件,即向法院发出批示或要求法院来汇报案件。这是政制基本规则。由于80%的案件由县区基层法院受理,中院是最重要的上诉审法院,再以中级法院所在的市为表述对象析之:不仅作为市委副书记的市长、有常委身份的其他副市长无权以组织方式介入法院案件,分管政法的副市长也无此项组织权力。市政府中虽然有一位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但其分管的是政府法制、公安、司法行政、信访等部门,对于国家安全机关、法院、检察院,职责仅是负责联系。依照中共党内“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组织原则,如果其向法院发出指示,不仅有违基本政制、组织原则,而且僭越了党委内分工政法工作负责人的职权,为政治纪律所不容。某些文学、影视作品,为夸大政府对于法院独立的干预,多设计副省长、副市长等官员要求法院汇报案件的情节,背离基本政治常识。以法律与文学材料理解中国司法的部分学术作品,亦以此为据,显与政制和实践不符。这些干部介入诉讼,方式是隐蔽的、私底的关说,起根本作用的是利益交换,而非组织制约。
其次,政府内计划、财政、人事等部门的实权派官员,虽对法院有局部工作约束关系,但此种约束如前文所述,已日益萎缩。由于法院负责人在职级上高出同级政府部门负责人半级,依照中国的政治架构,这些官员更不可能通过组织体系对法院审判进行批示,或要求法院院长、主管院长前来汇报工作。如果其出面介入诉讼,是俗称的“说情”,法院为之枉法,原因必然是货币贿买,或者这些部门负责人能够和法院院长、主管院长、庭长等控制案件的行政负责人进行利益交换,如安排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的亲朋好友或关系人就业、为关系人进行职务提拔或其他利益照顾。性质属于前述类型Ⅲ利用“脸熟”居间进行的贿请。
这即导致能提供给当事人,以组织方式向法院施压的官员具有稀缺性。另外两个原因导致该稀缺性进一步加剧:其一,前述中共中央严格实行干部避籍任职、不得在本人主要成长地任职等规定后,异地交流、提拔到本地任职的主要官员,对本地当事人来说是“陌生的异乡人”,短期内能建立超越组织关系的私密感情的人极少,搜索链过长。其二,任何现代社会都存在基于职业、职位、资本、出身、学历等各种因素所存在的社会分层,在社会分层的层级内,跨层级建立私密关系极困难。
因此,一方面,能对法院办理的案件有制约力,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有求于之,因而会听命于其指令的人,数量有限;另一方面,有人脉关系网络,能找到上述人物,并且能游说动这些人出面给法院施加有效的压力的诉讼当事人数量又极其屑微。虽然从党委、人大主要干部的社会交往而言,社会上必然会有与本地、上级党委、人大主要干部有私密关系的人,但因为政治、社会、组工纪律等各种限制,这种关系基本是极小范围获悉,不必然公开地招摇、示形于江湖。找到目标官员,方式往往是层层打听、托人,即使找到目标官员,该官员的品质德性,是否会接受该当事人贿买,又属于极不确定要素。因此,即使能找到目标,方式通常是:当事人→中间人1→中间人n-1→中间人n→地方党委政府中的关系人→法院,搜寻成本过大。当然,诉讼中具有这种搜寻能力的当事人是存在的,无法否定确有当事人能直接搞定市、县区委书记,但是,这种当事人还要考虑以下变量。
(二)贿买官员成本
当事人即使有能力可联系到这些官员,这些官员愿意出面向法院发出指令,当事人需要支付的成本极高,贿金大小既与受请的官员级别高低正相关,也和请托的案件标的大小成正比例。
(三)风险量值1
首先,与知识壁垒和专业化限制相关。地方党委、人大的官员,对诉讼所涉及的高度复杂化的实体法、程序法通常极为陌生,对案件的构成、证据、法律适用精微之处也完全隔膜,面对民商事诉讼专业槽日益细密、精深的普通法律术语诸如缔约过失责任、先合同义务、避风港原则、维斯比规则、INCOTERMS2010等都不明就里。所以,来自党委、人大负责人对正在办理案件的批示,即使要求限期报结果,并由有关部门督办的高级别领导人的函件,其所做的案件批示,都罕有技术性的直至案件中枢,而是内涵包容性大,并符合政治正确。多数只能是概括性、原则性的笼统提出要求“依法处理”,难以在极关节位置的证据、事实、法律适用要害处,直接点示。
其次,从社会心理上看,地方党委、人大官员介入诉讼,非因公共利益,而是受个人私下所托,居间向法院游说说情,这是一个分寸拿捏需极其细微的活动。对官员心理而言,从推动力上,因个人情面以及金钱利益驱使,势必要向法院打招呼。但是,一方面如前述,案件所涉证据、事实、实体法、程序法的法律适用高度专业化,官员的专业知识完全不匹配,因此,只能是笼统的提出请照顾,而不是具体的提出要求如何。另一方面,在官场上历练多年、升迁至一定职位的党政官员,都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经验:案件是双方争议,不能仅听请托人一方之辞,请托人通常有隐藏的私密信息不会透露。[22]所以,官员说情都有基本的限度,此限度的边界就是足以自保,不能使这种说情成为“硬说情”,从而导致自己陷于可能的被动。这种心理决定了官员的说情通常只是笼统的转告法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关照”。
再次,地方党委中能卡住法院的几位干部,其职权治下有干部职务提拔、房地产项目、工程发包或安排贷款居间等事项,此类事项既为他人办“好事”,又不存在“零和博弈”下有确定的利益受损者可能引发持续信访。与在诉讼中因为受贿压法院,导致对方当事人利益受伤相比,这些事项风险小的多。既然有可在“避风的”领域受贿这一“等功能替代品”,而且风险较小,所以,面对请托在民商事诉讼中打招呼,精明的党政官员通常会谨慎对待。实践中,党政官员对无法磨开情面的请托,采用的方式往往是将自己出面打招呼的行动,能让请托人明确知悉,即可交代得过去。
以上这些能被开放式地做各种理解,左右摇摆、摇曳多姿的批示、“打招呼”,与指向明确的附有“要结果批示”的转办函相比,差异明显,力度一望即知,而且可以被法官用精细的技术性知识所化解,对于当事人往往用处不大。这导致当事人贿买官员所支付的成本,具有极大不确定性,极有可能没有收益。
(四)贿买法官成本
这一环节,只有在第三个环节顺畅运转之后才能发生,如果在第三个环节,即“风险量值1”阶段风险发作,第四个环节即不会发生,此前当事人的所有付出,在该案件中全部沦为沉淀成本(sunk cost)。如果第三个环节顺畅流转至本阶段,其继续的逻辑如下:因为当事人所获收益并不正当,因此打招呼通常不是一般的以势压人,而是在沟通、搭桥之后,另由请托的当事人以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进行实质性的权力贿买。所以,即使在官员做出的批示转至法院后,当事人仍要不同程度地层层贿买法院的院长→主管院长→庭长→承办人,费用极高。
(五)案件直接收益
按照最高法院1999—2008年的民事经济案件管辖权划分,基层法院的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权极低,如在华东的安徽,合肥除外,包括沿长江经济发达的安庆、芜湖在内的各中院,受理以财产为内容的一审民事案件,争议金额为20万元以上不满3000万元;经济纠纷案件争议金额为40万元以上,不满3000万元。全国多数县区法院都执行20万、40万的标准。[23]40万、3000万,都是规划的最大值,在实践中,县区基层法院实际受理的经济案件中,能接近40万元标的上限之中线(即20万元)的案件都极少。2007年,全国法院受理民商案件472万件,案均标的金额15万元。[24]在争议标的额中,当事人有效利润又只占百分之几。为了区区几千、几万元的利益,当事人层层托人,请动一个县/区委书记、副书记,向法院施加压力,或可能产生效果,但成本收益付出不对称。
(六)风险量值2
首先,事情败露风险。在持续经年的批判“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呼吁“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口号下,民商事案件中的多数,由承办人提出意见并签发。如果是地方党委、人大中的领导人打招呼,根据经验中社会分层对等的规则,必然不是直接找没有脸熟机会的低职级的承办法官,而是直接找因长期共事、一起开会等原因而熟悉,并且级别职位相当的院长或副院长,再由院长、主管院长向庭长布置,庭长向承办法官布置。因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徇私枉法的发生,通常是层层寻租进行权力贴现,步骤通常是:诉讼当事人→(中间人1→中间人n-1→中间人n→)地方党委、政府中的关系人→法院院长或副院长→庭长→承办人,这一代理链条过长,交易成本过大,而且因为环节多,信息发散可能性大,风险高。在每一个环节链条,好处费层层转交,送给官员的好处费是赤裸裸的行贿。这种情形,如前述,在当事人对抗的条件下,发生明显偏离的诉讼结果,信息又极为分散,收受这种案件上的贿赂,败露的不确定性极大。
其次,二审改判风险。1990年代以来,各地为发展区域经济大规模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搭台,实现经贸唱戏,尤其是给招入本地的利税企业大户各种袒护。因此,具有极强的游说、交易贿买能力的地方企业是存在的。但是,即使一审中通过地方党委、人大压法院,造成请托当事人的有利结果,诉讼审级制度具有纠错功能,如果对方上诉至二审法院后原审胜诉方败诉,则一审中的巨额付出皆归于负数,整个风险量值2的阈值范围(0~∞)即直接发作为无穷大。
综上所言,通过贿赂地方党委、人大有支配权的3-5位官员,向法院施加压力获得胜诉,这在逻辑是通畅的,但是成本付出和预期收益之间的不确定性过大。即使所有环节走通,最后赢得胜诉,最后极容易落入“赢者的诅咒”(the winner’s curse)[25]这一困境。
五、一审程序中的上级法院介入
理性的当事人从不必然按照书斋安乐椅上研究者键盘敲击出的文字指示来行动。如果有两种以上方式(EU(B)i,i≥2)都可以实现(诉讼收益-成本)-风险量值>0,那么,当事人一定会选择(诉讼收益-成本)-风险量值诸方式中,效用最大的一种(EU(B)i>EU(B)i-1)。实践中,当事人更多选择是(案件胜诉收益-搜寻上级法院法官成本-贿买上级法院法官成本-贿买法官成本)-风险量值1-风险量值2>0这一种方式,而不是寻求地方党委、人大官员这一方式。
以前述的六个指标值,来测评贿买上级法院法官这一方式。
(一)搜寻成本
首先,与能对法院案件进行介入的数量有限的3-5位党政干部相比,在法院内部,因为审判关系,能介入一审法院案件的不仅是上级法院院长、主管院长,也包括对口的上级法院审判庭的内勤、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审判长(常任)、副庭长、庭长。由于中国法院编制的分布是倒置的金字塔型,级别越高的法院,人数越多,对口业务庭的上级法官数量层层递增,上级法院的千根线,都系在下级法院一根针上。目标数量较大。
其次,《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限制的地域任职回避,仅限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长(常任)、普通审判员、助审员,均不在避籍、回避主要成长地任职范围,这些法官管理者和法官生于斯、长于斯,血亲、拟制血亲、同学、亲朋、故旧在本地众多,对于当事人来说,低搜寻成本地找到一个上级法院目标法官,较之找到能“打招呼”的党政官员容易得多。
再次,搜寻到上级法院法官的概率极高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律师的居间。与前述搜寻到能与党委、人大主要干部进行居间的关系人十分困难的状态相比,能与法官居间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律师。而长期在各个级别的法院所在地,以诉讼为主营业务的律师,有相当部分与本人主场所在地的法院各庭法官有各种人情关系。这表现为以下形态:律师是合法、公开介入诉讼,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人员,以该身份为介质、桥梁,可以提供法律服务形式遮蔽之下的居间作用;某个律所和律师所提供的敞开式法律服务的内容和优势,以及律师个人的出身、交往等特殊关系,以名片发送、网页介绍、报纸广告以及餐桌饭局、聚会时的言谈夸口、博客、文章等各种方式广而告之,昭告天下;律师服务遵守“出租车排队法则”(cab rank rule),只要客户能支付得起费用,服务对象无差别,为任何向他们寻求服务的客户提供服务。[26]
最后,从可选择性看,如前述,法官与党政干部相比,党政干部事权较宽,有意贪腐的官员可在职位提拔调动、房地产项目、工程发包、安排贷款等多个领域,有受贿空间且风险较小,而有意贪腐的法官,唯有“吃案件”一途,较之党政干部,贪腐的法官对寻价的律师具有更强的迫切性甚至主动性,创租者和寻租者能在一起案件中心领神会,此后即一拍即合。
从搜寻成本角度审视,在实践中,法官和律师具有错综复杂的亲密关系,使得以律师为渠道找到法官,极为便捷。两者的亲密关系有以下形态:1.法官的配偶和子女从事律师工作,此现象极为普遍,以致需要连续发司法文件进行规范。[27]2.法官辞职、退休后担任律师或律所顾问,虽不得再在原法院进行代理,但是无法根绝帮其他律师介绍案件、牵线、分成。3.因强调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排斥从其他途径进入法院,律师和法官群体逐渐均为法学院科班出身者,许多法官和律师是法学院的师生、校友、同学,甚至同门师兄弟。4.法学院教师极高比例地担任兼职律师,而许多法官在法学院担任法律硕士兼职导师甚至博士生导师,法官在职读学位、到法学院参加业务培训,法学院教师到法院挂职,加深了彼此的业缘。[28]5.部分刑辩律师和法官,虽然没有亲缘、血缘、业缘、同学等紧密关系,但部分贪腐的法官,刻意结识部分不良律师,双方长期合作,彼此信任,结成介绍案件—利益均沾共享意义的“法律共同体”。
所以,在诉讼当事人游走、搜寻于各家律所时,寻获具有此种交易能力的律师极为容易。即使受托律师本人没有直接关系,寻找到目标法官都并非难事,原因是律师圈所发挥的作用。社会互动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圈子”。圈子的一个特征是内成员/局内人(insiders)彼此共享一些成员之外的人(outsiders)不知悉的信息、规则。从事诉讼业务较多的律师,对于圈内哪位律师与哪个法官或庭长、院长有特殊默契,大都心中有数心照不宣。只要当事人具有强支付能力,委托律师会直接与目标律师进行联系,以共同代理人的方式进行合作,收益分成。即使是案件诉至最高法院,寻找到与相关法官,甚至主管院长有私密关系的律师进行勾兑,都不断有案例披露。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被认定的受贿罪共五起,金额为390万元,其中四起为收受律师陈卓伦、陈文以及北京某高校教师赵某某的贿赂,向下级法院或本院承办人打招呼、作出书面批示。[29]
因此,从交易达成的可能性来说,通过地方党委、人大介入案件,除极个别有强交易能力的当事人之外,对绝大多数当事人属于不可能。而通过律师居间上级法院是普遍可以达致目标的行为。即使对于跨市、跨省诉讼,案件发生在本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之外、距离极远的外地法院,找到避籍、交流任职的当地党委、人大主要官员,几乎不可能,但通过法院所在地律师居间,与主审法官建立暗线联系,并非难事。在郑天翔院长做报告的1986年及此后的几年中,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极不发达,从业人员的社会活动能力也不足。因缺乏替代性手段,寻求以案外方式介入诉讼的当事人,求诸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官员,几乎是唯一形式,所以极其突兀。在律师数量从1986年的2万人上升到2014年的27万人,尤其是律师的来源、构成,以1992年为起点,逐渐发生大变之后,如果在诉讼中当事人意欲以非正当方式切入案件,对居间角色的扮演,党政官员基本被律师替代。
实践中,通过上级法院干涉案件的步骤通常是:当事人→律师→上级法院法官。这与前述通过贿买官员的方式相比,环节少,交易成本极低。
(二)贿买上级法院法官成本
假定与贿买地方党委、人大官员成本一致。
(三)风险量值1
上级法院对口业务庭的法官,对各种司法技能微妙之处了然于胸,进行的影响多直接、具体,且在法律上难以为旁人查知。在方式上,上级法院的主管院长、对口业务庭室的庭长、副庭长或分片的审判长,可以要求承办法院来汇报案件并简单阅卷,或直接调阅案卷,从而会对案件的证据、事实、法律适用,有准确的认知。不用如党政官员一样担心专业技术知识不具备,以及受到信息屏蔽,而被请托的当事人错误诱导下套。这些法官能直击要害,从单个的证据证明力、证明能力和系统性的证据体系,以及细致的诉讼程序和微妙的实体性构成事实、程序性构成事实等司法技术性知识切入,可以解构或重建整个案件的基本方向。从对诉讼当事人的收益来说,这种收益显然更大。所以,对于贿请的当事人而言,只要其贿赂到位,一般能得到预期收益。此前因知识格栅限制等导致地方党委、人大官员的踟蹰、犹豫,从而对案件具有的不确定性,在此降至极低。
(四)贿买承办法官成本
假定与前述通过贿买官员的方式切入上,成本一致。
(五)案件直接收益
与寻求党政官员的方式不变。
(六)风险量值2
首先,事情败露风险。对于律师居间的情形而言,贿赂是以委托律师的收费名义出现,尤其是对所谓“风险代理”,即根据事后判决所得收益,支付了极高诉讼代理费的案件,彼此对这种超高律师收费背后的因素都心照不宣。在风险防范上,从关系链条的第一环开始,违法性即被阻却。在关系链条的最末一段,因为律师和法官具有前述的各种血缘、亲缘和其他人身关系,不仅犯罪违法性再次被阻却,而且相较于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受贿,对这种亲密关系人之间的受贿,在该当—违法—有责的各环节,出罪的裂隙多,尤其是围堵、闭合证明标准对侦查的要求高,取证难度巨大。这对各角色的风险极小。
其次,二审改判风险。在前述诉讼当事人通过地方党委、人大打招呼,案件判决后,被上诉或抗诉到上级法院,如果被改判,则一审中的付出悉归于零。而通过上级法院对口业务庭向下级法院打招呼,事实上两审合一审,一次勾兑,两次受益。由于中国审判是两审终审,实际是一次勾兑,终身受益。
在此种方式上,有一个环节上微妙之处,即之所以诉讼当事人已搜寻到愿意进行权力贴现的上级法官,还要转而向下级法院打招呼,而不是坐等上诉至二审法院再改判,原因在于:1.除了法学课堂上研判的证据、程序、实体之外,法官优先考虑的是业绩测评考核,由于改判将影响到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考核、评比,牵连到的不再是某个诉讼当事人的个体利益,而是下级法院与本院的整体机构利益,因此一般不会轻易做出改判。2.一审判决后,二审如果仅维持原判,在二审法院内部,承办人即可决定,而如果改判,则要报庭长或主管院长审批,内控机制复杂,[30]这会导致寻租成本巨大。所以,诉讼中,对口的二审法院法官向尚在一审环节的案件承办法官打招呼,对于两级法院法官来说,结果都是最优:⑴一审法官不用担心判决有偏而被改判;⑵二审法官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内控机制最简单。因此,在许多案件中,即使当事人找到地方党委、人大负责人出面勾兑,一审法院中被请托人会告知其最好找一个上级法院的法官、庭长来出面,因为这样对一审法院也是风险最小。
所以,当事人诉诸于上级法院寻求“保护”,而不是诉诸于地方党委、人大、政府,是实践中最高频次发生的现象。
六、上诉审程序中地方保护发生的低可能性
前文分析以一审案件为对象。如果是二审案件,在目前两审终审制下,二审法院裁定即终结,那么二审法院所在的地方党委、人大,是否会被当事人更优先选中 经验测知,这种情形并没有超出上述分析,即寻求二审法院的上级法院的方式。
(一)搜寻成本
一个县区法院一审判决的案件,县区的当事人要在市一级寻找到能对法院有支配力的3-5位官员;中院一审的案件,要到省一级寻找目标官员。从社会分层意义上以及前述干部任职回避、交流制度导致的后果上看,跨越层级和地域找人,搜寻难度进一步增大,概率进一步减少。
(二)贿买地方党委、人大官员的成本
首先,一审已经败诉的当事人,二审想翻盘,成本付出会更高,因为二审如果不是裁定维持而是改判,如前述,变更一审判决,对于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来说,都影响业绩考评,所以,当事人贿买费用必须能弥补法官的业绩考评损失。其次,改判在二审法院内部,相对于维持原判而言,内控机制复杂,这进一步加重了当事人的寻租成本。再次,贿买官员的形态依然为:当事人→(中间人1→中间人n-1→中间人n→)地方党委、政府中的党政官员→二审法院院长或副院长→庭长→承办人,链条、环节仍然过长。加重了的成本,摊在各个环节。
综合以上三项内容而言,在中小标的案件中,通过党政官员方式进行的贿买,成本之大使得行为无效率,甚至抵销案件收益,从而使得贿买行为不足以开展。
(三)风险量值1
一审已经败诉,接受贿请的官员要干预二审改判,前文所述的知识格栅、社会心理等因素会更重,其干预会更迟疑、犹豫,从而导致启动二审法院改判的有效性更低。
(四)贿买承办法官成本
假定保持不变。
(五)收益
当事人从案件中获得的直接收益,亦如一审时发生的情形。
(六)风险量值2
这在二审时变得更复杂。虽然在诉讼收益上,因为两审终审,如能通过二审法院所在的省市党政官员搞定二审,当事人不存在败诉风险,但是,这变量受到以下因素影响,而变得不确定:
1.不管是哪种外力方式介入,对二审法院进行干预,可能忽略了案件证据、基本事实、法律适用对案件判决所起到的确定性。如果证据、事实、法律适用,完全不利于某一方当事人,而通过请托地方党委的方式专横干预做枉法裁判,是完全摒弃了三十多年来中国立法、司法解释进行规则之治的成果。如果一审法院证据确实、事情清楚,仅法律适用有错,二审法院可以径行改判;如果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优先适用“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其次是“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31]这是审级制度中初审对二审的反制约。该因素对于通过党政官员介入和上级法院介入的限制,结果一致。
2.自1982年以来,《民事诉讼法》规定,即使二审法院改判的案件,也由一审法院执行。二审法院粗暴蛮横地将一审法院判决径行改判,因为影响到一审法院考评,一审法院可能会进行反报。虽然改判的直接结果由某业务审判庭承担,但影响到一审法院院长的整体业绩考评,一审法院院长有多种方式使案件在本院执行局的执行环节,表面上“用力很大,但纹丝不动”,实际上得不到执行。
3.如果一审时一方当事人胜诉,二审结论直接翻转,判对方当事人胜诉,使得败诉当事人会直接甩掉申诉程序,而进行上访、闹访、媒体访。两份结论突兀对立的判决书会给观者以深刻印象,导致寻租方权力贴现活动败露的风险加大。所以,地方党政官员和上级法院法官都不会简单地被一个诉讼当事人的请托所绑架,作出强硬蛮横干预。
4.前文已述及,为何二审法院不是坐等上诉至二审法院再改判,而是提前介入至一审的原因,这一因素在本节论域中更突出。对于一方当事人通过请托地方党委、人大来干预本法院二审的案件,二审法官必须实现一个利益平衡,即二审法院、一审法院、二审法官、一审法官的利益平衡,机构和个人各方都没有利益恶化。如果一起原告胜诉的案件,被告通过请托地方党委向二审法院施压,导致二审法院将一审法院判决直接改判为被告胜诉,那么,在案卷评查、绩效考评时,一审法院和一审承办法官都可能因此被苛责或丢分,从而导致一审、二审法官之间关系不睦。这种简单破坏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行为,对于上级法院来说是极力避免的。因此,即使在二审时地方党政负责人介入案件,二审法官通常的作法是发回重审,或调解,使双方都各让一步,以回避以上各种风险。但如果是各让一步的调解,会导致诉讼收益降低,从而使得诉诸密集的寻租活动一方的当事人,没有效益。
由此,在上诉审程序中,当事人请托地方党委、人大官员依然是低概率发生的现象。
七、上诉审程序中的上级法院介入
如果当事人继续选择寻求二审法院的上级法院,相较而言,依然在成本收益上是有效率的方式,即一起县区法院判决的案件,对方当事人上诉至中院,另一方当事人会继续寻求、请托高院进行寻租,而不是在中院所在的市委、市人大寻找关系;如果是中院判决的案件,对方当事人上诉至高院,另一方当事人会继续诉诸于最高法院进行寻租,而不是在高院所在的省委、省人大寻找关系。这种行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反正式制度的,因为二审终审制下,二审法院对手上的二审案件说了算,不存在二审案件被三审上诉而被改判,但这是对中国法院上下级关系过于图式化的理解,这也正提示了时下中国法院上下级关系的非制度化。这种行动逻辑的根由在于:
首先,与美国严格区分初审、上诉审法院不同,中国地方各级法院都可受理一审案件,中院、高院,分别作为县区基层法院和中院的终审法院,每年都审理大量二审案件。这种一审和二审的错叠关系,使得中院、高院分别作为终审法院的同时,又在自己审理的一审案件中,接受高院、最高法院的二审。以中院为例,虽然中院对上诉案件是终审,高院对口业务庭对于时下手上的案件没有审级关系,即使是再审,也是由高院审监庭审理。但是,预期的长期交易合作关系,会影响时下短期行为的选择判断,上下级法院对口业务庭,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中的上诉审关系,而是一个长期的领导、指导、服从、支配关系,中院不会在一起个案或几起个案中,因一时意气而与作为上级法院的高院弄僵关系。对于作为二审的中院,虽然案件终审权在手,但是在其他自己一审的案件中,要服从二审的高院。
其次,除了上下级法院错叠的一审、二审关系之外,大量法院审级之外的支配关系,包括纪检监察、诉讼费上缴、组织人事任免、业绩考评、评查案卷、排名等各种手段,将上下级法院关系进行了重构。尤其是在上级法院不断的将庭长、副庭长下派到下级法院担任院长、副院长的背景下,上下级法院关系更远超过了《人民法院组织法》所限制的形态。
上述因素使得二审法院的上级法院介入二审案件,并享有支配力成为可能。对于(诉讼收益-成本)-风险量值>0这一公式进行拆解后的分析,表明这种可能会转化为现实:
(一)搜寻成本
与搜寻级别越高的党政官员越困难不同,当事人以律师为中介、居间,找到高级法院的法官,并不与审级增高而成正比例关系。
(二)贿买成本
一审败诉的当事人二审翻盘,成本付出比一审要高,但是相比于寻求党政官员,环节依然较小:当事人→律师→上级法院法官,比较成本同样较低。
(三)风险量值1
相比于寻求党政官员,通过二审法院的上级法院介入,在知识格栅限制和当事人从案件中获得的直接收益两个方面,都能给当事人带来更大回报,因为出现二审法院的上级法院这种情形,在四级两审制下,被选中的法院要么是最高法院、要么是高院。高院和最高法院的知识优势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中国审判实践中,实际起作用的规范,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最高法院正式公布的司法解释之外,在司法行动精微的中枢关节之处,是大量的非正式规范在起着极大的作用,包括各种座谈会纪要、批复、内部明传电报(通知)、政法机关的联席会议、标有密级的指示、主管院长在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级法院庭长、副庭长简单的口头电话意见,甚至具体操办案件业绩考评的内勤所提出的技术性要求。立法、司法解释在一地实施时的各种细微差异,只有同处于一个对口的审判领域的人员才能尽悉。这些非正式规范大多由最高法院、高院发布,高审级法院对口业务庭的庭长、副庭长、法官掌握有一定的话语解释权。
其次,审判中有大量无言的、隐蔽的司法知识,如果不是持久从事民事、商事、行政、执行某一个具体的司法领域的法官,即使是法学院中以此为专攻之术业的优秀学者和专业律师,都无法窥测、感知到。司法制度规则、实体法、诉讼法的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前述的各种非正式规范日益繁密,如果长时间未身在该具体审判业务序列之内,即使是法院内另外审判庭的法官,都难以洞悉案件的关节中枢。
因此,通过办理案件表现出来的与实体、程序等各种责任追究、考评,以及明确的、潜行的管控指标和印象管理参数,最主要的测评主体即是高院和最高法院。大量可以轻易拿来搪塞作为外行的地方党委、人大负责人的口实,完全无法作为抵御上级法院的借口。高院、最高法院相比于同级党委的知识优势表现的淋漓尽致。风险量值最低。
(四)贿买承办法官成本
假定与寻求党政官员相比,保持一致。
(五)收益
与寻求党政官员相比,保持一致。
(六)风险量值2
在此方式下,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和法律适用对于二审同样有制约,对方当事人信访的压力也始终存在。此外,二审法院的上级法院介入二审案件,翻转了一审判决结果,与党政官员介入的情形一样,同样会使得一审法院、二审法院、一审法官、二审法官业绩测评不利。但是,每一级地方法院的测评都是由上级法院作出的,中院的测评由高院做出,高院的测评由最高法院作出。如果一起案件的改判是由高院介入导致,那么高院势必会在考评时对此做出技术性处理,从而不使该中院利益恶化。最高法院介入的情形亦如此。这种内部测评上的变通关照,是法院体系之外的党政官员所不具有的。这降低了一审法院、一审法官对于二审改判后抵制的风险。
这种寻求二审法院的上级法院相对于寻求党政官员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一些极端情形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一方当事人的请托寻租方是上级法院,对方当事人的请托寻租方是地方党委,两种意见发生冲突,地方法院必须作出二择一的选择时,会选择倒向上级法院。制度性的原因在于长期交易互动的期待。在普遍实行党政干部交流、避籍任职制度之下,地方党委的负责人在一地任职,时间很短,几年时间即会升迁、转任,或实现隐含的层级内提升。这一组织人事上的政治设计,对于中国地方政治产生的影响之一,即是作为扎根于本地的法院法官,要考虑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地方党委的官员在任职避籍回避、任期制下,与上级法院相比,是“流水的地方党委”。虽然主管院长和庭长有轮岗的规定,但只是法院内部分工和有限庭室之间的轮岗,要求是任期满十年之后,而不是如党政官员异地交流,而且这种轮岗要求因出自法院内部自律,在多地是并未执行的柔软的规范。即使跨庭室交流,由于上级法院内设庭室分工更细致,从民一庭庭长交流到本院民二庭或民三、民四庭任庭长,对于下级法院民事口来说,依然是对自己审判业务进行领导的上级法院庭长。而且副庭长以下审判人员不属交流范围。所以,上级法院的主管副院长和庭长、副庭长、分管某片区的审判长,代表的是“铁打的上级法院”。
因此,对于二审案件的当事人,继续寻求二审法院的上级法院进行寻租,就是一种可期待的行为。在实现可能性上,这种期待同样是在成本、收益、风险量值的比值上,在地方党委人大和上级法院之间进行对比时,后者更有效率。当然,对于(诉讼收益-成本)-风险量值>0,这一公式中拆解出的六个指标值,单独看某一项,都容易找到例外,但是各种因素以乘积的方式,结构性的发挥作用时,寻求上级法院总是比诉诸党政官员有效率,因此成为作为理性人的当事人的优先选择。[32]
八、余论
以上只是制度逻辑分析,经验上的结论趋向与此基本一致。前述分析的结论,即寻求案外干预的当事人,寻求上级法院优先于寻求地方党委、人大负责人,获得了统计数据的支持。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检察年鉴》刊载的案件为检索对象,对从1987年出版以来至2012年期间,任职地方市、县区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会主任、副主任,包括政府正副职负责人,对其判决认定的受贿案件进行检索,没有发现一起受贿干预或影响民商事审判执行的,包括密集收受贿赂的被告人,如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受贿69起,累计970万,山东济宁副市长李信受贿40起,金额450万,安徽阜阳市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受贿30起,金额359万。仅有的两个例外,都不是批评和对策所剑指的县区、市,而是是省一级的官员,一起是贵州省委副书记黄瑶与其特定关系人李季秋共谋,对一起股权上诉案件打招呼,收受贿赂245万。另一起是曾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省人大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的王有杰,受贿干预河南高院对河南银基房地产开放有限公司与拆迁户回迁纠纷一案。[33]
对于人、财、物受制于地方的流行叙事,究其实,与经验偏差也极大。时下中院、基层法院院长高比例的来自上级法院的庭长,或副庭长下派任党组副书记几年后提任,而不是地方县区委、乡镇党委书记或局委办主任,这一现象本身就检证了地方党委“保护”能力的衰弱。就财、物而言,虽然对于法院“两庭”(审判庭、法庭)建设,财政多有倾斜性的保障支持,但法院每每以超出地方财政、经济、社会发展和其他本地局、委建设的水平,修建规模巨大的豪华办公楼,一旦地方财力无力支持,即被学界批评为法院财、物受制于地方。
当然,中国司法的表现具有极为复杂的面向。依目前的管辖制度,目前80%的案件由县区基层法院审理。两审终审制下,中院是绝大部分案件的终审法院。在时下政制语境下,对于有强大交易能力的当事人,勾兑县区、市级重要党政干部,给法院施压,目前的司法体制并不能抗制。对于有极强的能力建立权力贴现、货币输送关系的大资本所有者,制度设计尤无法防止。如果扩大样本收集范围,细致筛查,找到市、县区地方党委、人大负责人干预司法的例证,是不困难的。但是,对于地方保护这一相比较而言低概率、小比例发生的现象,研究者给予了过度的倾注,上级法院也极力将高概率、大比例发生的上级法院干预现象虚化,置于地方保护主义的阴影之中。2008年,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执行难的原因主要有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法律制度不够完善。[34]原湖南高院院长吴振汉也提出:“应尽快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以避免司法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35]但此后两人均因重大受贿犯罪而案发,分别被判无期徒刑、死缓,犯罪事实中多有干预下级法院案件。由此可见,原本是上级法院常态性的干涉下级法院案件,但培育多年的地方保护主义话语成功地将批评锋芒转致到外部的地方党委、人大、政府,遮蔽了最高法院对全国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在审判、执行上,以个体利益为目的进行不当干预这一经常现象。
在中国政制架构下,地方各级法院,在制衡关系上,出自于两个方向:⑴垂直方向,来自于上级法院的“上诉审——审判监督”关系;⑵水平方向,来自于地方党委和人大的领导,以及同级政府对经费、物质保障上的制约。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三十年来通过“法院—研究者”话语互动,不断反对地方党委、人大的领导和政府的制约,形成具有控制性的反地方保护主义话语形态,在后果意义上,水平方向上的制衡逐渐弱化、淡出。缺省的空间,被研究者自然而然地理解为转而由上级法院担当,促使决策层颁布政策,或支持法院自己出台新政策,加强最高法院对全国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统管,使得垂直方向上级法院的支配权膨大,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控制强化。这改变了中国地方司法政治的结构,为今后地方政治治理带来新的趋向。
[1]郑天翔:《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6年4月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8年4月1日)
[2]Randall Peerenboom,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The role of Courts in China , in John Garrick(ed.), Law and Policy for China’s Market Socialism, UK, Oxon: Routledge, 2012,p174;Yuwen Li,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umbling Towards Justice,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14, p159.
[3]《中国统计年鉴(1986)》,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4] 高培勇主编:《中国财税体制发展道路》,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3页。
[5]前文称地方政府可能构成玩忽职守,即是此情形,在主管局委领导国企时代,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的若干意见(试行)》(1987年8月31日)规定的诸罪状之一“上级主管单位领导人,对明知是违反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财务制度规定的收支决定办理或者坚持办理,情节严重,给国家造成损失在五万元以上的。”
[6]《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通过)。
[7]《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8]《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
[9]《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1995年2月9日,第38、39条;《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1998年地(市、州)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跨省交流工作的通知》,1998年7月8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年7月9日),第53条;《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2006年8月6日),第5条;《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的通知》,2011年12月12日 中组发[2011]31号。
[10]“担任县(市)委书记、县(市)长职务以及县(市)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年7月9日),第53条。
[1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1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通知》,中发[1991]14号,1991年7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厅字[1994]2号,1994年1月30日。
[13]《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通知》,2002年8月30日,厅字[2002]7号。
[14]参见《关于人民法院在人、财、物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的报告》(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江华司法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
[15]《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考试录用工作的通知》,2004年11月19日·组通字[2004]50号;《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关于印发〈公开选拔初任法官、检察官任职人选暂行办法〉的通知》(2008年8月14日)。
[16]限于篇幅此处大幅删减,可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09]3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政法经费分类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财行[2009]209号;中央政法委员会政法研究所:《司法在改革中前行》,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页;谢旭人主编:《为国理财 为民服务——党的十六大以来财政发展改革成就(2002-201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250页。
[17]《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党组关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法律体系有关情况的报告〉的通知》(2011年4月12日),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办公厅等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4-1529页。
[18]实践中一些案件,外地当事人因具有比本地当事人更强的贿买能力,导致案件裁判结果极大的偏离常规,向外地当事人利益大幅倾斜。
[19]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20]考虑到不同内容之间有认知的先后次序,不按照公式各项的顺序展开。另外,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批评集中在民商诉讼内,本文亦仅以民商诉讼为分析。
[21]《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印发〈关于在市、县、乡换届中推进领导班子配备改革有关情况的通报〉的通知》,2006年12月31日·组通字[2006]50号。
[22]传于民间的一则传统司法笑话是:某人上控,称因捡拾路旁的草绳被处杖刑。上级官员指斥下级官员暴戾枉法,但调阅案件才知,草绳后栓着一头牛。
[23]《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各高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标准》(1999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10号,2008年2月3日)
[24]《2007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说明》,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3期,第24页。
[25]竞价者为赢得胜利,支付了高于价值的估价,虽然胜出,但过高的出价导致收益不足以抵偿。见[美]理查德·H·泰勒:《赢者的诅咒——经济生活中的悖论与反常现象》,陈宇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59页
[26] [美]理查德·L·埃贝尔:《美国律师》,张元元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27]《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庭(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事有偿法律服务活动和商务活动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27号,2000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的通知》,法发[2011]5号,2011年2月10日。
[28]《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法发[2004]9号,2004年3月19日。
[29]《中国检察年鉴(2011)》,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540页。
[30]北京高院规定:“改判的案件,合议庭应听取一审人民法院的意见。”“维持原判的案件,合议庭成员意见一致,可以由合议庭作出决定。”“改判案件,应当向庭长汇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办案规范》第292、300、304条,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编:《审判工作规范》,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18页。
[31]《民事诉讼法》(1991年4月9日通过,2007年10月28日修订)第153条。2012年民诉法修改(第170条),此部分稍改。
[32]香港城市大学贺欣教授提出质疑,比如华为对于深圳,财税关涉较大。地方党委对异地企业在本地提起的诉讼势必过问。本文认为如案值千万元级或以下,则对于本地财税影响极小,官员权衡损益,收益不足以使地方干部冒风险启动干预。如案值过亿,根据级别管辖一审即由省高院立案,超出市的支配范围。虽然深圳负责人职级高,但省内有分管事项差异,且二审至最高法院。非单独计量一个指标,而以本文的公式计算各因素的乘积后,此种可能性并未构成例外。
[33]参见《中国检察年鉴》2002、2006、2011、2012、2009年卷,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第419、441-444、549、475、430页。
[34]《高法高检有关负责人接受集体采访 改善司法环境 促进司法公正》,载《人民日报》,2008年3月16日,第9版。
[35]吴振汉:《避免司法权地方化行政化》,载《人民日报》,2004年3月7日,第7版,“两会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