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角落:乡村老年的“隐性离婚”
一.名存实亡的“银发婚姻”:农村老人的隐性离婚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对数达到了287.9万对,相比上一年增长了1.4%。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10.0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77.9万对。2023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对数达到了360.53万对。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 259.37 万对,法院判决、调解离婚101.16 万对。近些年来,离婚率虽然因为疫情和离婚冷静期的影响有所回落,但总体呈现不断攀升趋势。据J市某城郊村的一位三十多岁的村干部说,他小学42名同学中,认识的17个人里14个都离婚了。无论是从客观的数据分析,还是从访谈对象的主观感知出发,都可以明显观察到离婚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无论学界还是实务界对离婚问题的关注,均局限于村庄场域的中青年一代,对老年群体的婚姻及情感状况进行了选择性的忽视。事实上,乡村老年群体中存在的婚姻问题的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中青年一代,一种“隐性离婚”形态正在困扰着基层社会。
在村庄场域中,老年人受困于村庄舆论和对离婚的污名化,不会轻易就去离婚。但是现实中却发展出了隐性离婚的形态,隐性离婚即农村老年夫妻通过协议离婚或事实分居,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解除婚姻关系,但出于家族体面、子女利益或村庄舆论压力,对外仍维持婚姻表象的行为。这种现象既包含法律层面的“隐性离婚”,即已领离婚证但秘而不宣;也包含事实层面的“隐性分居”,即未解除法律关系但实际终止婚姻生活。在隐性离婚之下,双方看似还是夫妻,但实际上各过各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实际离婚率远高于统计数据。某村村干部私下透露:“10对声称‘感情不合分居’的老人中,至少有3对早已悄悄离婚。”这种“隐性离婚”往往通过错峰务农、分灶吃饭等细节,在村庄熟人社会的缝隙中悄然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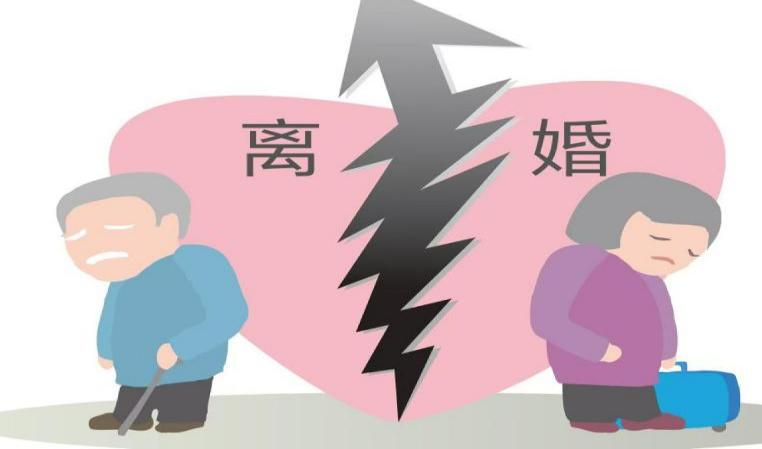
二.农村老人隐性离婚的特征
1.离婚不离家
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为反馈模式,讲究均衡互惠的原则。即在代际间由父代抚育子代,子代赡养父代,下一代对上一代进行反馈,也就是所谓的“养儿防老”。在这种家庭代际关系结构之下,农村老人的养老主要依托家庭,由儿女承担。在有余力之时,农村老年人仍然会帮助儿女分担生活重担。由于受制于各种因素,农村老年人虽然已无婚姻之实,却依旧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维持着双方的基本体面和生活的日常运转,即离婚但不离家。离婚不仅意味着个人情感上的断裂,而且代表着双方法律关系上的切割。但从代际关系、经济层面和生活维度看,离家则需要对生活进行更加彻底的清理和重整。
此外,从经济共同体层面来看,农村老年夫妻捆绑的更为紧密。在农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这些农村老年女性一旦离婚是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也不大可能继续留在夫家继续居住。先依附于父、后依附于夫,受制于时代的规训,她们更多是没有能力离婚,离开了那个泥坑,又没有去处。“我妈已经陷入帮我哥哥带孩子的生活中,没有收入,身体不好,需要靠我爸每个月给生活费,我爸还在努力打工帮我哥还结婚欠下的债,农村的他们还处于离婚是很丢人的状态,不过现在因为他们各司其职的忙碌生活,也没有精力像年轻时候那样争吵甚至打架。”在现实面前,农村老年女性很难成为“出走的娜拉”。
农村老年人受制于多重因素,离婚并非易事,从而发展出“离而不分”的关系形态。如下述“我父母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离婚。我爸生命最后几年得了老年痴呆,母亲虽然痛苦,但依然坚持照顾一直到送走他。我爸走了之后,我和哥办他的身后事,买墓地时,我妈很认真地对我们说,以后她走了不想和我爸葬在一起,还要离得远远的。我想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离婚”。又比如,“去年年初,我爸出轨被我妈亲眼撞见。之后,妈妈陷入了严重的抑郁,因此决意离婚。离婚后他们仍然居住在一起,我无法苛责我妈,身为女性,她经历了她的时代的规训,经历了漫长的亲密关系里的纠结和挣扎,是这些塑造了她的能与不能。”
农村老年离婚的典型特征是“物理空间重叠”与“社会关系割裂”并存。原来村里有个老头频繁家暴老太太,但是老太太的要求是让村妇女主任把他俩隔开,一个住二楼,一个住一楼,井水不犯河水。这种空间上的安排既规避了宅基地分割难题,又维持了“完整家庭”的体面。究其原因在于农村老年女性的经济依附,“代际-经济-空间”的三重捆绑,使得离婚成为一场无法彻底完成的仪式。
2.情感需求与搭伴养老的耦合
传统关注的重点在于对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和身体照料,但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物质需求满足之后,老年人对情感需求的关注日益增多。老年人在情感上的孤独感、归属感、社交需求成为当下的新需要。传统农村通常是多代同堂,老年人虽然随着年老而带来的劳动能力下降,但是在整个家族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但现在随着以宗族、家族为基础的大家庭迈向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结构形式的转变,农村传统的三代扩大家庭也渐渐发生着改变,形成现今的新“三代家庭”。即父代和子代在分家之后形成一种事实上“分而不离”的家庭代际关系,分家由过去的实分变为“虚”分,这是在转型社会中家庭发展压力之下的策略性选择,因为子代可以从这种代际关系中获得多方面的收益。
在“分而不离”的代际结构下,子代虽通过经济支持与虚拟分家维系着形式上的赡养责任,却难以填补父母的情感空洞。低龄老人为子代提供隔代抚育时,尚能依托孙辈的亲密互动获得情感补偿;而一旦步入高龄、退回村庄成为“完成使命”的空巢者,伴侣关系的质量便直接决定晚年生活的精神底色。当婚姻无法提供情感慰藉,离婚虽成为解脱选项,但乡土社会规范又迫使许多老人转向“搭伴养老”的折中方案——通过非婚同居等形式,在规避法律与道德风险的同时,实现情感慰藉与生活照护的隐秘平衡。这种耦合既是对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性补充,亦暴露出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化诉求与集体伦理的持久张力。
3.法律风险的存在
在这些新形态的婚姻关系下,产生出各种复杂的实践和风险因素。一方面,农村老人在年轻结婚时由于当时程序不完善,很多都没有结婚证,在村里办了结婚仪式和酒席就算结婚了;即使领了结婚证,后来也早已遗失,档案也不复存在。根据法律规定,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条例》公布实施以前,按事实婚姻处理。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双方愿意补办结婚登记,否则只能到人民法院起诉,不能前往婚姻登记部门办理协议离婚。通常农村老年人法律意识较薄弱,没有在法律上解除婚姻关系便找另一半,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婚姻关系。这种双重事实婚姻关系造成后续继承混乱,加剧纠纷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容易产生代际矛盾与财产纠纷。比如有的农村老年人可能为了避免给子代增添麻烦而选择搭伙过日子的同居不领证方式。在这种模式之下,则会产生新的代际冲突,老来夫妻与各自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容易引发新的矛盾与纠纷、长期同居下也容易引发高密度的利益纠纷。例如,老人将宅基地房屋赠与同居伴侣,其子女可能以“家庭共有财产”为由主张无效;而长期共同务农形成的经济积累,因缺乏婚姻关系保护,在分手时极易引发“劳务补偿”争议。

三.农村老人隐性离婚的成因
人的行为是受观念影响的,而人的观念则受制于既有的社会结构,所以农村老年群体的隐性离婚是由村庄社会基础塑造的。在城镇化背景下,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村庄内的人口总体呈流出趋势。由此村庄形成了一定的内部分层,青年群体由于上学、就业、婚恋等基本处于县域以上的城市中;中年群体往返于城乡之间,虽然“身”处城市之中,但“关系网”仍在村内,兼顾上下两代的需求;老年群体则扎根于村庄之中,生于斯长于斯。在华北平原的农业型村庄,村庄内人情往来和社会联络得到了基本的保留,仍然具有一定的村庄公共性和舆论约束力。在村庄内人群分层之下,“在场”与“不在场”对于不同群体的离婚现象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
1.村庄舆论的压力
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老年人,兼具“身体在场”和“关系在场”的双重属性。村庄老年人是真正处于村庄场域之中的,他们与村庄关联度和紧密性最强,具有强烈的村庄认同感,受到村庄内生秩序和村庄舆论的影响也最深。村庄中的老年人离婚很少,特别是被村庄内其他人知晓的更是罕见。相较于城市中老年人的“退休之后就离婚”,农村中老年人离婚显然更不容易。尤其是农村老年女性群体,她们没有稳定的退休保障和独立的房产居住,衰老之后一旦离婚便无处可去,即使身处困境也只能在岁月的黄沙里被慢慢埋没。但是,她们是在面子上维持婚姻状态,维护的是婚姻的名而非实。
“上个月老公的奶奶过世,我们回家奔丧,我父母还坚持要在这种场合给我挣面子,处理丧事时他们都一起露面,帮着忙前忙后。两个人也能客客气气地聊聊天,寒暄一下。虽然父母已经离婚,但该给的面子大家都会给。 ”又如“我七十岁提出了离婚,协议都双双签字了。儿子不同意,没办离婚证,但心里面已经离了。互不干涉,经济独立,但为了儿子的面子,还得委屈自己。”在这背后是传统宗族观念与个体意识的激烈纠缠。大多农村老人都会认为离婚会让家族蒙羞。就像被蛛网困住的飞虫,他们既想挣脱婚姻枷锁,又怕扯破那张名为“体面”的关系网。
2.服务于代际关系的老年婚姻
在打工经济盛行之下,村庄内老年人的“工具性婚姻”占据主导地位。当家庭资源不断向子代输送,夫妻关系退化成“合作社”。老年婚姻逐渐异化为代际利益的传递工具,在本质上是“代际接力赛”中的一环。在完成举债盖房、为儿娶媳、扶养孙辈等“人生任务”后,老年婚姻的工具性价值消退,矛盾集中爆发。据观察,村内近些年来有好几对是在完成“人生任务”后立刻解除婚姻关系的。代际压力之下的婚姻犹如情感荒漠,一旦失去代际压力这个“外力”,婚姻就像被压到极限的弹簧一样瞬间崩解。代际压力曾作为粘合剂强行弥合夫妻裂痕,其消解后的婚姻关系犹如失去重心的陀螺,在惯性中走向溃散。许多老年夫妻在子代成家后迅速陷入“任务后真空”,既无共同目标牵引,亦无情感纽带缓冲,最终选择解除法律或事实上的婚姻联结。
六十多岁的王大妈家里因为大儿子娶媳妇欠了20万外债,老两口一个进城当保洁,一个在工地搬砖,十年间见面不超过十次。“去年他腰伤了回村,我俩睡一屋整夜不说话——他嫌我做的饭咸,我嫌他打呼噜响,可谁都不敢提分开,怕儿子在城里被人笑话‘爹妈都管不住’。”
3.平衡既有社会关系的需要
离婚必然会破坏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破坏在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尤为致命。农村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多重社会关系的交织。婚姻关系承载着远超情感维系的工具性功能。一旦离婚公开化,断裂的不仅是夫妻纽带,更会引发连锁反应。所以农村老年人选择隐性离婚,本质上是对社会关系资本的策略性保全。他们通过精密计算离婚的“关系成本”,而选择隐忍。这种隐忍的本质,是将个人婚姻自主权置于代际利益和家庭社会关系稳定之下。尤其当子女面临婚嫁关键期时,父母甘愿成为“婚姻演员”——在提亲时并肩而坐展示和睦,在婚礼上配合敬酒营造圆满,以此换取子女在乡土社会评价体系中的“正常家庭”认证。这种代际牺牲,既是对传统伦理的妥协,亦是在现代化冲击下维系社会关系网的无奈之举。
六十余岁的李某和妻子在儿女都已成人之后就分开居住生活,两人已经保持这样的生活十年有余。两人性格都很强势,经常吵架甚至有时大打出手,因为李某的一次醉酒后家暴,其妻子终于下定决心与李某协议离婚并逐渐分开生活。但至今村里人大多都不为所知,因为他们的小儿子还未结婚,所以他们严格保守“秘密”并扮演好父母的角色。如果被人知道就会在婚恋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为了不给儿子“添堵”,李某和妻子会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状态,直至儿子能够顺利成家。

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幸福晚年的未来
在当今的离婚潮之下,老年群体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然而,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出现愈来愈多的农村老年人离婚。相比于青年群体的闪婚闪离、中年危机下的熟年离婚,老年人的银发离婚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当城市老人拿着退休金追求“夕阳红”时,农村老人正用最原始的方式,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重构婚姻的意义。面对着现实的情感需求,发展出法律和事实层面的隐性离婚等多种关系形态,并随之带来一定的风险后果。农村老年离婚从来不是简单的法律关系的解除,而是乡土社会现代转型的温度计。当最后一代被宗族伦理规训的老人逐渐老去,或许我们会看见——在与现代性的碰撞中,那些曾困在婚姻空壳里的灵魂,终将找到安放自我的新可能。
隐性离婚的婚姻形态暴露了传统婚约制度与现代社会规范的断裂。现行有关婚姻方面的法律以“登记制”为基础构建权利义务框架,但对“事实婚姻解除”、“隐性分居”等非典型婚姻状态缺乏回应。当一对农村夫妻在民政局解除法律关系后仍以夫妻名义同居,法律既不能强制其公开离婚事实,亦无法规制由此衍生的财产混同、继承纠纷等问题。更尖锐的矛盾在于,法律追求的“形式正义”与乡土社会所需的“关系正义”产生冲突——判决离婚可能瓦解一个家族三代人的社会资本,而维持婚姻假象又损害个体权利。当法律与现实错位、社会规范与个体诉求脱节时,隐性离婚游离于制度监管之外的灰色地带。它既非传统的婚约伦理所能包容,又非现代法律体系所能规训。如何突破隐性离婚困境,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