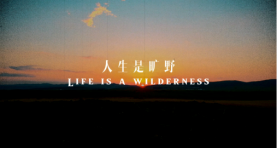体制内工作:西藏社会的“成功标配”
旦巴伟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春节假期,我回到家乡,走进堂弟的房间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颇具时代特色的画面:他盘腿坐在卡垫上,面前堆满了《申论宝典》和《行测必刷3000题》,藏式矮桌上的平板电脑正播放着粉笔公考的网课。我打趣他:“怎么突然这么用功了?”他笑着回应:“当然了,去年考公的人数比转山年的朝圣者还多。”这句玩笑话背后,折射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近年来,考公务员、进入体制内的热潮愈演愈烈,成为无数年轻人追逐的目标。的确,在西藏这片土地上,体制内的工作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在这里,考体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选择,更是一种社会风尚和价值取向。与其他地区相比,虽然考体制同样是众多求职者的重要选择,但在西藏,却能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过度的考试压力和浓厚的考体制氛围,呈现出了一种“唯体制论”的职业选择取向。家长们对孩子的考体制问题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他们不惜花费重金,为孩子报名参加各种公考培训班,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在未来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有的家长甚至在孩子还未踏入大学校园之前,就已经开始为他们未来的考公之路做足了准备。他们让孩子提前了解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和要求,培养他们的应试能力和综合素质。更有甚者,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在考公时更具竞争力,还会特意让他们报考一些特定的大学。这些大学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已经投身于公务员考试的准备之中,他们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参加各种模拟考试和培训课程,以提高自己的应试水平。
如此种种,使得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异常浓厚的考体制氛围。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访谈了众多家里的亲戚长辈、业已毕业的同学朋友和师弟师妹及其它们的家长,并在社交媒体上找寻了有关该话题的讨论资料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希冀对西藏的考体制问题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二、西藏体制内就业热潮社会观察
(一)“体制突围”的发展策略: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
体制内工作,通常指的是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具有稳定编制和福利待遇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因其稳定性、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对完善的福利体系,而备受求职者青睐。在西藏,体制内工作更是被视为“铁饭碗”,成为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选择。
其中,从普遍的价值观念出发,三类体制工作亦有价值次序的排定:公务员位于职业金字塔的顶尖位置,是所有人优先竞争的选择,其包含有通过“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而认定的国家公务员和通过“省考”(西藏自治区公务员考试)而认定的省级公务员;而后是事业单位的工作,抛开对口专业的考生大多数人是在考公失利或者无法考公的情况下会涌入事业单位的就业渠道实现上岸的理想;排在最后的是在国有企业谋求生计的工作,在国有企业中,求职者同样能够找到稳定的工作岗位、可观的薪资待遇以及丰富的职业发展机会。然而,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由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业地位更为显赫,因此国有企业的工作往往被视为体制内工作的“备选方案”。
(二)“海拔不重要,编制才重要”的择业观念
从过去的“宁死只留城镇”到“只要考上就是奇迹”,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就业观念的转变,人们对于工作地域的考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过去,人们在选择体制工作时,往往会将工作区域的生活水准和环境优劣作为重要的评析因素。因此,拉萨、山南、林芝等生活质量相对更好的城市和市区周边地区成为了求职者的首选之地。而那些偏远地区,如日喀则亚东、阿里等,则鲜有人问津。然而如今,随着体制内工作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人们就业观念的逐渐开放,地域生活情况在求职者的综合分析中的比重已经大幅下降。对于许多人来说,只要能够获得体制内的工作机会,无论身处何地都愿意欣然前往。这种转变体现了人们对于体制工作的渴望与执着。
(三)体制内工作:西藏社会的“成功标准”
在西藏这一独特的地域环境中,体制工作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稳定性,更被赋予了极高的社会意义,形成了一种“唯体制论”的职业选择取向。在这里,体制内工作早已超越了一份普通职业的范畴,它成为了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一种精神上的寄托,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
进入体制内工作,意味着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这种认可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稳定的收入、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体制内工作被看作是一种“体面”的职业选择,它象征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因此,许多人将考入体制内单位视为实现自我价值、赢得社会尊重的必经之路。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在西藏,没有体制内的工作,就像没有‘身份’一样,别人看你的眼光都不一样。”
此外,体制工作还承载着家庭和家族的荣耀。如果一个家庭的孩子能够考上体制内的单位,那么这个家庭在整个社区中的地位也会随之提升。父母和家人在与其他人交往时,会因为孩子的成就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这种荣耀感不仅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也进一步强化了整个社会对体制工作的认同和推崇。一位来自日喀则的母亲在访谈中提到:“儿子考上公务员后,村里人见到我都会主动打招呼,连以前不怎么来往的亲戚也开始走动。这种感觉,比什么都值。”
体制工作在西藏已经被高度理想化,成为了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家庭家族的荣耀以及人生成功的标志。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西藏社会对体制工作的极度重视,也揭示了体制工作在西藏社会中的核心地位。
(四)体制内工作的身份标签
在西藏社会,体制内工作逐渐被异化为一种鲜明的“身份标签”,进而催生了由体制内工作这一标准而产生的社会分层结构。体制工作,作为国家建设和吸纳精英人才的重要途径,因其招录门槛高、资源有限,注定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层层筛选,获得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资格,而大多数人则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沦为“陪跑者”。在“唯体制论”这种偏颇的职业观念影响下,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分类体系:人们根据是否在体制内工作,将劳动者简单粗暴地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阵营。
对于体制内的工作者来说,无论他们身处何种岗位、在何地工作,只要头顶“体制内”的光环,便能轻松赢得社会的高度认可。相反,体制外的工作者,无论他们的薪资待遇多么丰厚,工作能力多么突出,往往都会被先入为主地贴上“非体制”的标签。即便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体制外的工作者也能获得一定的社会评价,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他们始终难以获得与体制内工作者同等的尊重和认同。这种基于工作身份的标签化现象,在西藏社会愈发明显,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风貌。

三、西藏体制内就业热潮生成原因
(一)结构性动因
西藏地区体制内就业热潮的持续升温,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结构动因。体制内工作以其优厚的待遇、稳定的职业前景和全面的保障,成为吸引求职者的关键因素。在西藏,与市场化岗位相比,体制内工作不仅能够提供更高的薪酬和更完善的福利,还能在职业发展上给予更多的安全感。尤其是在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体制内工作的稳定性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面对市场波动,还是突发公共事件,体制内的员工都能享受到更为可靠的收入保障和职业安全,这种“旱涝保收”的优势让体制内岗位成为众多求职者的首选。
相比之下,市场化岗位在西藏的处境则显得尴尬。由于地理位置偏远、经济结构单一,市场化岗位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满足当地求职者的需求。薪酬水平普遍偏低,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够完善,这让许多求职者对市场化岗位望而却步。与内地城市相比,西藏的就业市场缺乏灵活性,优质企业数量有限,进一步压缩了求职者的选择空间。
与此同时,传统行业在现代化浪潮中正逐渐失去吸引力。许多传统职业,如寺庙僧人、唐卡画师、藏式木匠等,因技术革新或市场需求的变化,正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年轻人接触了更多的现代元素,接受了更为开放的教育,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渐减弱,更倾向于选择与现代生活节奏契合的职业道路。这种趋势不仅让传统行业的就业渠道变得越来越窄,也让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断层的危机。
这种经济结构的失衡,加上传统行业的式微,进一步加剧了体制内就业的热度。年轻人被推向了一条看似“唯一正确”的职业道路,而其他可能性则被逐渐边缘化。
(二)代际影响
在家庭环境中,代际传递的“风险厌恶”心理深刻影响着子代的职业选择,尤其是父辈对市场化就业的不信任态度,成为推动年轻人涌向体制内的重要力量。父辈们基于多年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和职业风险有着深刻的认知。他们或许经历过行业的兴衰、企业的裁员,甚至亲眼目睹过市场化就业的脆弱性。这些经历让他们对体制外的工作充满了谨慎,甚至恐惧。于是,“稳定”成了他们为子女规划职业时的最高准则。
在这种观念的潜移默化下,子代逐渐接受了“体制内工作才是稳妥选择”的逻辑。父辈们不断强调体制内的好处:稳定的收入、完善的保障、体面的社会地位。相比之下,市场化就业则被描绘成充满风险的“未知领域”。这种观念在子代心中扎根,使得他们在面对职业选择时,往往更倾向于听从父辈的安排,将考公务员或进入事业单位视为“唯一正确”的道路。
此外,家庭中的权威结构和代际依赖也强化了这种顺从。在许多西藏家庭中,父辈不仅拥有更多的生活经验,还掌握着家庭资源的分配权。他们的意见往往被视为不可置疑的权威。当父辈对市场化就业表达出不信任时,子代即便内心有所犹豫,也很难提出异议。接受访谈的一名大学生无奈地说:“我知道自己可能更适合做设计,但父母觉得不稳定,非要我考公务员。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只能硬着头皮去考。”
这种代际传递的风险厌恶心理,不仅塑造了子代对职业稳定性的追求,也让体制内工作成为了家庭共识中的“最优解”。然而,这种选择背后,往往隐藏着年轻人对自我兴趣和能力的牺牲。正如一位连续三年备考公务员的年轻人所说:“我其实不喜欢这份工作,但父母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我只能告诉自己,稳定比喜欢更重要。”这种无奈的选择,体现了代际观念对个体职业自由的深刻影响。
(三)个人成功的追求
在探讨西藏“体制热”现象的成因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许多人将考取体制内职位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这种观念的背后,是西藏社会对成功的单一化定义——考上体制,便意味着个人的成功。这种“唯体制论”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体制内工作不仅代表着物质上的稳定与保障,更象征着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广泛的社会认同。在朋友、亲戚、家人面前,拥有体制内身份往往被视为一种荣耀,仿佛戴上了一顶无形的光环,象征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种“面子文化”的影响,使得考上体制成为了一种体面且有尊严的选择,随之而来的是话语权的提升和社会评价的显著提高。
成功考取体制,被视为个人努力和才能的直接体现,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实现和成就感的内在需求。在这种心理机制的驱动下,许多人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备考中,试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自己的“成功梦”。

四、青年自我认同危机
西藏体制内就业热潮的兴起,让“考体制”逐渐成为许多人眼中实现自我价值和提升社会地位的唯一出路。这种价值观的扭曲,不仅催生了人们对体制内工作的过度追捧和依赖,也引发了一场深层次的自我认同危机。
对于那些未能“上岸”的人来说,考体制失败不仅仅是一次考试的失利,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缺失,甚至是一种人生的挫败。访谈中,一位年轻人无奈地说道:“每次亲戚聚会,只要我没考上公务员,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连话都不敢多说,生怕被问到‘现在在哪儿工作’。其实我挺喜欢现在的工作,也是自己努力争取来的。”这种单一化的评价体系,无形中构建起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编制高”的畸形价值观,将体制外的职业选择贬低为“次等选择”。
许多人在考公失利后,会选择进入其他行业作为过渡,但他们依然会时刻关注体制内的招考动态,随时准备“跳槽”。即便他们在体制外的工作中表现出色,甚至获得了不错的职业发展机会,许多人仍然会选择放弃,转而投向体制内的岗位。几乎人人都认为只有进了体制,才算真正“上岸”。
在这种环境中,许多人也难以获得自我和解。为了迎合社会的期待,他们不得不做出许多本不需要的调整,甚至忽视自己是否真正适合体制内的工作。很多人也即使最终选择继续干下去,好像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差点意思。
当社会评价体系无法给予体制外工作足够的包容和认可时,许多青年便难以获得真正的自我认同,无法形成对自我的真实认同着实是一种痛苦。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不仅划分了职业的高低,更在无形中割裂了社会的认同感,让许多优秀的人才因“体制外”的身份而被边缘化。这种分化,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活力,也让许多年轻人陷入了“非体制即失败”的焦虑之中。
五、结语
西藏地区的“考体制热”是特殊时空背景下的制度供给与社会观念的共同作用的产物。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就业市场狭窄、代际传递的“稳定优先”观念,以及“唯体制论”背景下的单一成功观三者交织成一股强大的推力,将年轻人推向“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体制战场。这一状况本质上是边疆地区社会转型时期的过渡现象。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体制内工作并非唯一的选择。
青年本应是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群体,他们本应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理想去追求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只要是自己热爱的、适合自己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值得被尊重。然而,在“唯体制论”的裹挟下,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兴趣与梦想,盲目跟随潮流,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一条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甚至并不喜欢的道路上。这种被迫的选择,不仅消磨了他们的活力,也让他们失去了本该拥有的鲜活与多样性。很多人拼命挤进体制内,并不是因为真正热爱这份工作,而是因为“没有其他退路”。与其说他们是在为自己争一口气,不如说他们是在害怕——害怕没有体制身份的自己会被社会边缘化,害怕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
如果可以比喻,那么考体制失败就像一场生活的潮湿与阴霾,笼罩在年轻人的心头,阳光似乎很难再照进来。这种无形的压力,压抑了个体的创造力与活力。当所有人都被逼着走上同一条路时,那条路再宽阔,也会变得拥挤不堪,而那些本可以绽放光彩的多样人生,却在这股洪流中被悄然淹没。